「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在黃昏起飛。」黑格爾藉這句話提醒我們:真正的智慧,尤其是理解歷史的智慧,往往要等到塵埃落定,我們有時間回頭審視時才會浮現。
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要判斷其歷史意義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被自己的情緒、希望和恐懼所束縛,受限於對事態的有限認知,受制於掌權者對敘事的強大影響力,也無從知曉未來的後果——因爲這些原因,我們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形成深思熟慮的判斷。因此,人們喜歡引用前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名言。1972 年,當有人問他對四年前法國五月風暴的評價時,他只淡淡回答:「現在下結論還太早。」確實如此。冷靜的思考,往往勝過倉促的評論。
也因爲這個原因,過去一年出版的兩本書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它們分別嘗試從不同角度解讀 2020 年夏天在西方民主國家達到高峰的那場社會與文化動盪。(對這場動盪的稱呼本身就帶著強烈的立場。根據說話人的身份與態度,有的稱它爲「社會正義」或「反種族主義」,有的稱之爲「身份政治」或「取消文化」,還有人稱它爲「種族清算」「交叉性」或「大覺醒」(Great Awokening)等。)
《我們從未覺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
穆薩·加爾比(Musa al-Gharbi)著
從理論上看,我們的社會似乎比以往更加強調平等:偏見成了禁忌,多元文化備受推崇。然而現實中,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卻不斷加劇。
在《我們從未覺醒》中,穆薩·加爾比指出,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密切相關,且都與一種新精英的崛起有關——他稱之爲「符號資本家」。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432 頁。
托馬斯·查特頓·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的《我們不滿的夏天:確定性的時代與話語的消亡》(Summer of Our Discontent: The Age of Certainty and the Demise of Discourse)是一部結合歷史與新聞寫作的作品,從 2008 年講到 2024 年,重點圍繞 2020 年針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的社會反應展開。而穆薩·加爾比(Musa al-Gharbi)的《我們從未覺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則採取社會學與理論的路徑,運用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的既有分析範式,來爲其大膽的論點辯護。
這兩本書之間有不少相似之處。二者都由著名出版社(克諾夫〔Knopf〕與普林斯頓)出版,裝幀精良、研究扎實,也都有一批你意料之中的知名人物撰寫推薦語: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泰勒·科恩(Tyler Cowen)、尤瓦爾·列文(Yuval Levin)。兩本書文字敞亮、可讀性強,目標讀者是那些思考嚴謹但並非專業學者的普通讀者。作者都對他們所分析的社會發展提出批評,但更渴望理解,而非只停留在譴責層面。更重要的是,這兩位作者都是四十歲出頭的有色人種男性,對右翼民粹主義保持尖銳批判,因此並不能簡單地被歸類爲「種族反撲」的一部分。兩本書都十分傑出:深刻、好讀、富有挑戰性並具有啓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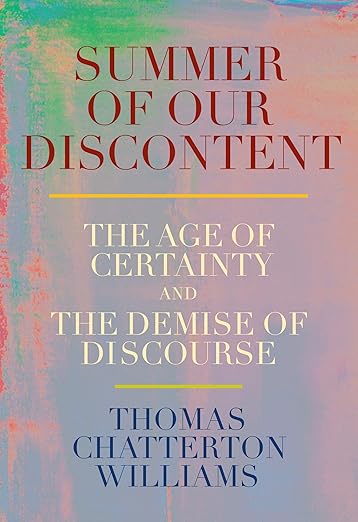 《我們不滿的夏天》從 2020 年 5 月 25 日弗洛伊德遇害那天寫起。那一幕幾乎已烙印在世人心中:一名白人警察以膝壓頸的方式壓制一名黑人男子長達九分半鐘,直到他窒息而亡,而這一切被拍攝下來,瞬間在全世界傳播。然而,威廉姆斯給出了一個不同且重要的視角。他指出:「喬治·弗洛伊德是個窮人。這是他生命中最顯著的事實」(第 xiv 頁)。「喬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不必、也不一定完全是因爲種族……他的死亡與他的貧困狀況密切相關。他因此喪命,是因爲一張大多數黑人一輩子都不會接觸到的假鈔」(77 頁)。
《我們不滿的夏天》從 2020 年 5 月 25 日弗洛伊德遇害那天寫起。那一幕幾乎已烙印在世人心中:一名白人警察以膝壓頸的方式壓制一名黑人男子長達九分半鐘,直到他窒息而亡,而這一切被拍攝下來,瞬間在全世界傳播。然而,威廉姆斯給出了一個不同且重要的視角。他指出:「喬治·弗洛伊德是個窮人。這是他生命中最顯著的事實」(第 xiv 頁)。「喬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不必、也不一定完全是因爲種族……他的死亡與他的貧困狀況密切相關。他因此喪命,是因爲一張大多數黑人一輩子都不會接觸到的假鈔」(77 頁)。
威廉姆斯進一步主張,我們有必要區分兩個「弗洛伊德」:一個是真實而複雜的弗洛伊德;另一個則是簡化後、成爲社會象徵的弗洛伊德。「一方面,他是某人的兒子和兄弟,在那個長週末過得很艱難,無業,體內含有甲基安非他命和芬太尼……在車裡打盹,幾分鐘前剛用假鈔買東西」(第 4 頁)。「另一方面,則是被永恆化的弗洛伊德,他的死亡定格在影像裡,在我們腦海中不斷循環播放……那是多年來一直醞釀著的、關於黑人刻骨之痛與白人至上主義沉重枷鎖的觀念。」(第 5 頁)
在他悲劇的時刻過去短短几分鐘,前者便幾乎完全被後者吞沒。數小時之內,人們便以近乎基督受難的方式來感受和理解他的死:
難道弗洛伊德不是以一種直觀可見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脖頸和肩膀承受了他所在社會的種族罪孽那可怕的重負嗎?而那重負,就是我們所有人罪孽的總和,難道沒有反過來壓垮他嗎?有一個人爲我們死在那骯髒的人行道上,他沒有問『父啊,你爲什麼離棄我?』而是令人心碎地呼喚他的母親。那位遲鈍的行刑者……彷彿洗淨了自己的雙手,將它們深深插進口袋」(第 7 頁)。
隨後的幾天和幾週裡,爆發了數千起抗議活動,數百萬人走上街頭,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這引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問題:爲什麼會這樣?
威廉姆斯通過講述西方世界自 2008 年以來的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並突出了四個關鍵因素。
在威廉姆斯的敘述中,能全身而退的公眾人物寥寥無幾。正如我們所料,他對川普的批評毫不留情。從他在任期間普遍的謊言與無知,到具體建議用光療法治療新冠肺炎甚至向人體注射消毒水等荒謬言行。
但威廉姆斯在許多方面對進步派左翼當時應對措施的抨擊更爲激烈。「在短短兩週內,我們幾乎未加深思熟慮地,就從譴責人們上街遊行,轉向譴責他們不上街遊行,」他寫道。這種思想上的混亂,至今仍在讓我們付出代價。
威廉姆斯特別關注 2020 年盛行的「反種族主義崇拜」——從羅賓·迪安傑洛(Robin DiAngelo)、伊布拉姆·X. 肯迪(Ibram X. Kendi)和尼科爾·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的理論建構,到普林斯頓大學的機構性懺悔、明尼阿波利斯市削減警局預算、《紐約時報》的強制辭職、波特蘭的表演性反種族主義等現實後果——這一切在八月的基諾沙事件中達到高潮:在雅各布·布萊克(Jacob Blake)遭槍擊後,CNN曾因其將現場描述爲"激烈但基本和平的抗議"而臭名遠揚。
威廉姆斯隨後將我們帶入當下,通過章節探討了美國反種族主義思潮通過社交媒體的全球輸出、取消文化、一月六日國會山事件,以及 2023 年 10 月以來的以色列與加沙衝突。威廉姆斯輕而易舉地表明,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都被 2020 年那個帶著強烈種族顏色的夏天深深影響了。
《我們不滿的夏日》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威廉姆斯的敘事功力很強,善於在熟悉的事件中穿插不爲人知的細節;他文筆流暢,時而閃現智慧火花;恰到好處的幽默多少衝淡了那段歷史所帶來的陰鬱與不快回憶。
然而,本書最缺失的正是盼望:盼望這段令人不適的故事不僅是集體性的災難記載,盼望現狀已經或即將改善,希望我們確實從過往中汲取了教訓。(不過平心而論,對於標題帶著「不滿」、副標題寫著「消亡」的著作,我們本就不該期待它會有昂揚的基調。)
有些讀者會發現在一位從容的敘述者引領下重溫那個夏天,能帶來某種釋然,畢竟五年後的今天我們都還安然無恙。我自己就是如此。但也有些人可能會渴望更多:一些積極的跡象、一條前路、某個令人鼓舞的案例,或某種大膽的新提議。對他們來說,這本書恐怕無法滿足這些期待。
《我們從未覺醒》裡處處可見大膽的論斷。當西方世界普遍認爲自身在 2010 年代至 2020 年代初經歷了「大覺醒運動」——無論人們對此歡欣鼓舞還是痛心疾首——穆薩·阿爾加比卻以冷靜而堅定的態度回應道:不,事實並非如此。
有些人假裝自己覺醒了,也有些人真心以爲自己覺醒了;另一邊,則有人猛烈批評、甚至嘲笑「覺醒」及其追隨者。但在加爾比看來,那場所謂的「大覺醒」根本就沒有發生:
我們中有些人假裝經歷了一場覺醒的過程,或真誠地相信自己已經覺醒。另一些人則猛烈批判或嘲諷這場覺醒及其所有追隨者。但實際上,那場所謂的「大覺醒」根本就沒有發生:
簡而言之,問題不在於「符號資本家」過於覺醒,而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覺醒……這些符號資本家經常做的事,反而是在利用、延續、加劇、鞏固、甚至掩蓋各種不平等,而且往往傷害的正是他們口口聲聲要替之發聲的人。我們對社會正義的真誠承諾,卻爲這些行爲披上了一層本不配擁有、且極具誤導性的道德外衣。(第 20 頁)
爲了論證這一點,加爾比引入了幾項社會學術語,其中最重要的是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這個概念指的是:我們在社會層級中因聲望、認可、榮耀與地位而擁有(或不擁有)的各種資源。這種資本可能來自我們在某組織中的職位、信譽、經驗或別人對我們的信任;也可能來自學歷、閱讀、學位、畢業院校、專業權威;或是文化性的,如語言、穿著、舉止、品味、觀點、術語等等。
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覺醒已成爲當代精英的一個重要文化資本」(第 26 頁)。文化精英之間辨識彼此地位、並展示自身地位的一種方式,就是他們在種族、性、性別、殘障、身份認同等議題上的立場,以及他們表達這些立場所使用的語言。
在文明社會裡,以特定術語表達的進步觀點,通常被視爲高地位的象徵。然而,這些觀點通常對他們聲稱代表的人群幾乎沒帶來實際好處;反而常常成爲自我服務、自我鞏固地位的手段。正因如此:「符號資本家與他們主導的機構,其表面上的覺醒程度可能遠高於實際情況」(第 36 頁)。
這種表象與現實脫節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性別議題上:許多人公開高喊「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但在現實中,當涉及約會或婚姻選擇時,他們的行爲並不反映這一信念。在經濟議題上:2011 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看似是一場草根反不平等抗爭,但主要參與者其實是報酬優厚、從全球化中獲利的高學歷「符號經濟」從業者。在種族議題上:近年來企業和大學推行的「多元、公平、包容」(DEI)計劃,獲益最大的不是底層員工或弱勢學生,而是那些擔任「社會正義鐵飯碗」(social justice sinecures)職位的專業人士(107–110 頁)。
環境政策方面,美國那些最進步的都市區,新建住房反而更少,警務執法更爲嚴苛,不平等現象也比其他地區更爲嚴重。婚戀觀念上,對傳統家庭抨擊最猛烈的人,往往自己恰恰成長於這樣的家庭,並且最終組建的也是類似的傳統家庭。慈善捐助層面,富裕的進步派人士將其收入用於慈善的比例,低於受宗教動機驅動的郊區及鄉村保守派,而且他們的捐贈更少流向貧困社區。
無論你看向何處,符號資本家們都在聲稱代表貧困和邊緣群體發聲,而實際受益的大多是他們自己的荷包。因此,「非精英階層最好忽略符號資本家們的言論,轉而觀察他們的實際行爲。」
話雖如此,《我們從未覺醒》並不是對進步主義的猛烈抨擊。書中雖揭露了大量故作姿態和虛僞行徑,尤其在關於圖騰式資本主義和受害者競相比慘的那章中,但阿爾-加爾比並未陷入黨派之爭的咆哮,他更傾向於選擇解釋,而不是謾罵。
例如,他坦然承認自己也是符號資本家階層的一員,並意識到反覺醒陣營與覺醒陣營同樣熱衷於標榜姿態和符號表演。他梳理了過去百年間四次"覺醒浪潮"的相似之處,通過突出其間的多重對應關係,證明了過去十年的變化其實並不算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是,他將表演性的覺醒視爲一種社會現象認真對待並探尋其根源。他先是闡釋「精英過剩」現象(99–103 頁),即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多於可提供給他們的高位工作,會因此產生怨氣,又進一步分析了「創意階層」的興起(134–146 頁),然後討論了「奢侈信念」(用來彰顯精英身份,卻往往傷害窮人)與「道德許可」(持有某些觀點能當作防止被指責爲種族主義的護身符),並將這些現象串聯成連貫的整體(270–295 頁)。
全書筆調細膩審慎,論證均以實證研究和量化數據爲支撐,並附有長達百頁的參考文獻。
然而他的論述始終清晰明了,不拖泥帶水,也不閃爍其詞。關於批判性種族理論的這段論述就是個絕佳範例:
被反對者貼上「批判性種族理論」標籤的這套思想體系,顯然不是弱勢階層和受壓迫者的語言。它不屬於貧民區、拖車公園、衰敗郊區、後工業城鎮或全球貧民窟。恰恰相反,這些思想主要受到高學歷且相對富裕的白人群體青睞,其中混雜著心理學與醫學的治療性話語、記者與活動家的干預主義、法律與官僚體系的繁瑣技術性表述,以及現代人文學科中僞激進的諾斯替主義。這完完全全就是符號資本家的專屬話語。(274 頁)
嚴謹的研究、清晰的文筆與緊湊的論證貫穿全書,是一本賞心悅目的好書。
威廉姆斯和阿爾-加爾比都未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他們的目的在於描述現狀而非開出藥方,這本身無可厚非。但相較而言,阿爾-加爾比更接近於指明前進方向,或者說提供了我先前所說的那種希望。
部分原因與兩本書的結尾氛圍有關。《我們不滿的夏天》的後記談到 10 月 7 日哈馬斯襲擊事件及其後續,讓人感覺世界似乎被困在永無止境的厄運循環裡;而《我們從未覺醒》的結語則提出了一些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方向,使人隱約看見可能性。這種差異也與時間尺度有關:威廉姆斯講述的是十五年間的故事,阿爾-加爾比描繪的則是百年週期,最近這輪動盪僅是其中一例。這種長鏡頭能爲作者與讀者都提供急需的視角,讓我們更冷靜地看待過去的動盪十年。
在我看來,另一重差異源於隱含的人性觀。《我們不滿的夏日》描述的是發生在我們身上、以我們之名上演的事件,作爲讀者的我們至多只是旁觀者,在華盛頓、明尼阿波利斯或紐約時報大樓發生的荒誕情節面前搖頭嘆息,我們被動目睹事態發展,能做的微乎其微。
相反,《我們從未覺醒》的核心主角正是我們自己。我們就是阿爾-加爾比筆下的符號資本家——否則也不會閱讀這樣的著作。稍加反思便會發現,書中描繪的諸多虛僞、地位博弈與道德矛盾,正是我們自身的寫照。正因爲作者與讀者身處同一困境,我們才能內化並反思阿爾-加爾比隱含的詰問:我們在哪些地方把行動主義變成了表演?我們的道德邏輯在哪些地方變得自利?我們究竟有沒有把自己所宣稱的理想落實在與身邊有需要之人的真實關係裡?他們是誰?我們是否謹慎,不讓自己的義行成爲表演?還是我們已經「得了該得的賞賜」?
歷經五年沉澱,人們普遍意識到 2020 年那場社會激盪走得太遠了。疫情過後,從覺醒資本主義、取消文化到無意識偏見培訓和跨性別權利,諸多議題都出現了明顯的反彈。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與社交媒體氛圍已發生深刻轉變。
但從另一面來看,這場變革又遠遠不夠。許多種族不公依舊原地踏步;許多改革只是表面功夫,結果反而讓更富裕、更受教育、更特權的群體受益;許多弱勢者依然在等待真正的覺醒降臨;許多教會在 2025 年依舊保持著 2019 年的那種涇渭分明的狀態。
這兩本書都無法單獨解決這些問題。但它們——尤其是阿爾-加爾比的著作——能夠通過重構那個動盪年代的敘事框架,挑戰我們的認知並帶來新知。前提是,我們需以謙卑之心(「主啊,是我嗎?」)而非自義之心(「感謝主,我不像那個符號資本家」)來品讀。時代思潮屢經變遷,未來仍將如此。對過往冷靜深刻的思考,終將幫助我們在下一次浪潮中做出智慧的回應。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ave We Ever Been W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