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基督教的無神論者中,有不少人認爲,相信上帝的信徒有認知方面的問題。「新無神論者」的代表道金斯在他《上帝的錯覺》(The God Delusion)一書中說,成年人相信上帝真的存在,就像小孩子相信聖誕老人或獨角獸存在一樣,是一種「錯覺」(delusion)。當然,這樣的看法並非道金斯首創,在他之前已經有一些著名的「老無神論者」對宗教有過類似的批判,比如弗洛伊德和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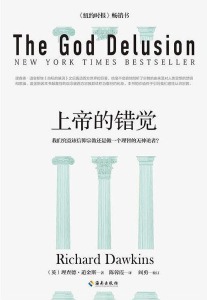 弗洛伊德通過精神分析方法,得出相信上帝的宗教信仰是源自「願望滿足」(wish-fulfillment)的結論。弗洛伊德認爲,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結」使他們對父親既有愛也有懼怕和敬畏,這種情結可能通過一個父親的替代物來抒發。在作爲人類「兒童期」的原始社會中,動物圖騰就是父親形像的替代物。
弗洛伊德通過精神分析方法,得出相信上帝的宗教信仰是源自「願望滿足」(wish-fulfillment)的結論。弗洛伊德認爲,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結」使他們對父親既有愛也有懼怕和敬畏,這種情結可能通過一個父親的替代物來抒發。在作爲人類「兒童期」的原始社會中,動物圖騰就是父親形像的替代物。
隨著歷史的發展,古代人崇拜的對象逐漸被人格化,最終人格化的上帝取代了圖騰的位置,宗教由此產生。因此,在弗洛伊德看來,源於人類在兒童期的慾望與無能的宗教,究其本質,是「一種普及的、強迫觀念型的神經質病」。
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我們可能更加熟悉。他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但很多人對這句話的含義其實是有誤解的。馬克思說:「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沒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是沒有靈魂處境裡的靈魂。它是人民的鴉片。」(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實際上,馬克思在這裡主要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和其中的統治階級,馬克思認爲他們是現實苦難和人性異化的根源。馬克思表達了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他認爲,宗教對於社會,就像那個時代被用於止痛的鴉片對於病人或受傷者一樣,具有緩解痛苦的作用。馬克思認爲這是宗教在實用主義意義上的一種功效。
儘管「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本意可能被人誤解,但馬克思對宗教的主要看法仍是負面的。他認爲,宗教作爲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用來麻痹人民、維護自己統治的工具。鴉片雖然可以減輕疼痛,但它給人帶來的其實只是一種暫時快樂的幻覺。在馬克思看來,宗教是人的認知過程失序造成的「對世界的一種變態的意識」——也就是說,相信上帝是一種認知上的病態。
宗教信仰是一種認知上的病態嗎?相信上帝是不是一種精神疾病的症狀?美國分析哲學家普蘭丁格在其著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中譯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中,針對這個問題,回應了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普蘭丁格指出,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都把宗教信念視爲反理性的認知,是因爲他們認爲宗教的存在來源於人的認知官能(cognitive faculties)失調而不能產生正確的信念,導致關於上帝的信念變成錯誤的迷信。
但是把相信上帝視爲一種認知失調,甚至精神疾病,在理性上是缺乏根據的。絕大多數有宗教信仰、相信上帝的人,都是精神正常的人,他們對世界的很多其他認知都沒有問題。他們能夠跟他人正常交流,在自己的工作上可能有優秀的表現,能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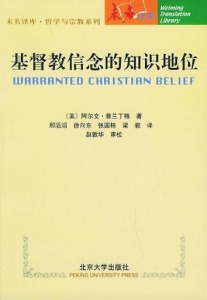 到他人(包括信仰不同者)的尊重。他們有很多理由認爲自己對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實際上,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包括基督徒)會反過來認爲,否認上帝存在的無神論信仰,才是認知出現問題導致的不合理的信念。
到他人(包括信仰不同者)的尊重。他們有很多理由認爲自己對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實際上,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包括基督徒)會反過來認爲,否認上帝存在的無神論信仰,才是認知出現問題導致的不合理的信念。
所以,爭議的核心是:相信上帝存在或者不相信上帝存在,到底哪一個才是人本來應該有的正常認知?這首先是一個哲學上所謂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問題,而知識論正是普蘭丁格的哲學研究所專注的領域。
針對現代西方哲學對宗教採取的邏輯實證主義的態度,普蘭丁格指出,即使上帝的存在不能在邏輯實證的意義上被證明,對上帝的信仰仍然是理性的,並且是「可以得到保證(warrant)的」。(「保證」是普氏用的一個哲學術語,用來取代「證明」。他認爲有「保證」的信念才可能是真知識。)普蘭丁格認爲對上帝的信仰是「正當的基本信念」,就像一個理智正常的人相信「2+2=4」或者「今天早上我的早飯是稀飯和包子」一樣,無須經由其他更基本的真知識來證明,卻是正當而合理的。
「恰當功能」的認識論
普蘭丁格發展出了一種「恰當功能(proper function)」的認識論,論證對上帝的信仰可以獨立於證據而得到保證。他認爲,一個信念能得到保證的必要條件,是賦予人「形成信念與維持信念的能力」的認知器官必須正常地工作,而我們的認知官能,例如感知、記憶和推理,跟我們「被設計的藍圖」及合宜的認知環境相關。只有當這些認知器官恰當地發揮功能,而我們的認知環境也正常的時候,我們的信念才有保證,我們所信的才可能成爲真知識。
普蘭丁格用「阿奎那/加爾文(A/C)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來論證有神論信仰的合理性。他同意神學家加爾文的觀點:因爲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創造的,所以人有「神聖感應」(sensus divinitatis),上帝藉著大自然和人類良知的普遍啓示,把「宗教的種子」播種在人心中。這是人能夠認知關於上帝的事情的基礎。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罪性的干擾,相信上帝的存在本來是人應該有的「自然」的正常認知。然而,因爲人背逆上帝、犯罪墮落,理性受到罪的污染,因此就認識上帝而言,人的認知官能可能失調,喪失恰當發揮功能的能力,導致無神論等錯誤的信念。普蘭丁格也同意加爾文所說,除非人接受上帝的特殊啓示(聖經及其見證的基督),除非聖靈在人心中做更新和重生的工作,人無法靠自己的理性對上帝有正確的認知。
普蘭丁格不但正面建構他的認識論,而且滿有智慧地運用他的這一理論回應無神論者在認識論方面對基督教信仰的批判。他挑戰無神論的自然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的哲學前提,指出無神論信仰無法爲人的認知器官發揮恰當功能提供根據:
既然我們只是由(沒有引導的)進化拼湊出來的,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就很難是完全準確的。自然選擇只對適應性行爲感興趣,它不關心信念是否真實……唯物主義是關於人類的:「人是物質的對象,而不是連在身體上的非物質的自我或靈魂或實體。人身上的部件不包含任何非物質的實體。」由此看來,我們相信什麼取決於神經生理,我們的信念是某種複雜的神經生理結構。這個神經生理無疑將是具有適應性的。但爲什麼道金斯們(無神論者)認爲這樣的依賴神經生理的信念多半的時候會是真的?他們爲什麼認爲我們的認知官能是可靠的呢?……
從自然主義的觀點來看,相信我們的認知官能可靠的看法最多只是一種天真的希望。自然主義者可以合理地確信信念形成背後的神經生理具有適應性,但這絕不等於基於這樣的神經生理而形成的信念就是真的。實際上自然主義者必須承認一點,那就是:「如果進化是沒有引導的,我們的認知官能就不大可能是可靠的。如果進化是沒有引導的,我們可能生活在世界之中而能夠真地認識關於自己的某些事情、也認識這個世界,但我們也同樣可能生活在一個夢幻世界裡面。」
因此無神論信仰在認識論上必然陷入自相矛盾,「自然主義是自毀長城,是違背理性的信仰。」
而相信上帝存在的有神論信仰則沒有這個問題:「從有神論的觀點來看,我們會預期我們的認知官能是可靠的(大部分時候是這樣,當然有一些限制條件和例外)。上帝按照他的形像創造了我們,我們因此像上帝,可以形成真的信念,可以獲取知識。」
故此,如果我們的正確認知是基於認知器官的「恰當功能」,那麼相信我們的認知器官是上帝創造、所以有「智慧設計」的有神論,比相信我們的認知器官是從沒有目的、沒有方向的漫長進化而來的自然主義無神論,更能爲「恰當功能」提供保證,也更能爲「人是否以及怎樣能夠認識關於上帝的事」提供更合理的根據。
因爲普蘭丁格的認知理論汲取了加爾文對人類認知的看法,符合改革宗神學的觀點,所以他的理論被稱爲「改革宗認識論」。實際上,加爾文的觀點也不是原創,而是來自聖經。聖經一方面告訴我們,雖然神是個靈,肉眼不能看見,但他「永恆的大能和神性」彰顯在大自然和人心中,「從他所造的萬物中可以領悟」;另一方面,聖經也指出「不虔不義」的罪人必然會「壓制」關於上帝的真理,因此雖然上帝已經向罪人顯出他存在的證據,他們仍然「不尊他爲神,也不感謝他,反而心思變爲虛妄,愚頑的心就迷糊了」(參《羅馬書》1:18-23新譯本)。普蘭丁格的認識論在這些方面是完全符合聖經的。
普蘭丁格一生恪守敬虔的基督教信仰,治學嚴謹,爲人謙和,連很多不認同他的理論的非基督徒哲學家都非常尊重他。而他對邏輯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等無神論的哲學基礎的批判尖銳犀利,並且富於睿智和幽默。他對無神論者的宗教批判的回應,是基督徒爲信仰辯護非常寶貴的參考資源。
本文原載於《海外校園》第1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