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要幫助我們的讀者「讓這幾個世紀以來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譯註)。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只有通過閱讀經典」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接下來要審視一些可能被遺忘、但是依然和現今的教會相關,並且能幫助今日基督徒的經典著作。本文是邸立基所著《神學第一步》(A Little Exercise for Young Theologians)的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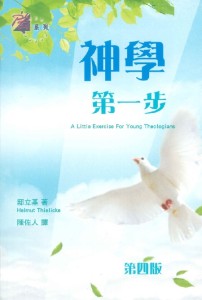 試著把這本小書想像爲一張賀卡,它的首要作用是給到那些剛踏上攻讀神學第一學期的人,祝賀他們一路順風(bon voyage)。同樣地,這本書亦可作爲祝賀「週年快樂」之用,對那些誠實的牧者,願意謙卑地回顧反省自己是否達到最初的目標。另外,此書又可用作祝那些驕傲自大神學家「痊癒」的賀卡,或極端點說,這可作爲一張慰問卡,安慰那些已經忘記整個神學任務所應有的興奮與應許的人。
試著把這本小書想像爲一張賀卡,它的首要作用是給到那些剛踏上攻讀神學第一學期的人,祝賀他們一路順風(bon voyage)。同樣地,這本書亦可作爲祝賀「週年快樂」之用,對那些誠實的牧者,願意謙卑地回顧反省自己是否達到最初的目標。另外,此書又可用作祝那些驕傲自大神學家「痊癒」的賀卡,或極端點說,這可作爲一張慰問卡,安慰那些已經忘記整個神學任務所應有的興奮與應許的人。
在剛才那段文字裡,「神學」一詞曾出現三種不同的版本(神學、神學家、神學任務——譯註),故此便細緻地反映了本書的宗旨:作者以清晰有力的語言,來表述深奧的神學語言。如果本書只用以歡迎年輕的神學家,那它就不會長久被當做紀念品來收藏。我們必須經常重讀此書,才能窮盡它的意義。作者期望那些初出道的神學家能從中獲得有用的規勸。
任何人在接受勸告之前,很自然地會審查輔導者的資格。看看他憑什麼這樣說,究竟他會向我說教?抑或將他的意見漸漸滲透進我的意識?他會否裝腔作勢?還是假作慈悲?在這情況下,他是否就知道神學與青年神學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在基督教的圈子中,鮮有人會像邸立基(Helmut Thielicke)般令我們給予毫不猶豫的信任。他身穿數個職事的禮袍,而且全部都稱身如意。譬如最近他出任德國漢堡大學的校長,需要負責一般行政職務,正如他在書中述及,另外他亦要穿上具有歷史性的學術袍子。作爲實用神學家,他要穿上教授的袍子,以便從事基督教倫理的講授工作。大部分讀者最喜愛的是他穿上講道袍的樣子,有些人則將他列爲世界上最偉大講道家之一,眾所周知,每星期兩次在世俗化漢堡城的偌大教堂,都因他講道的吸引而擠滿了人,德國的教章與雜誌都可爲此作證。他的講章現已有許多印刊成書,是許多傳道人拿來充實自己的少數書籍之一。最後,我們可以想像邸立基穿上燈芯絨的運動外套,作爲旅行家與說故事者,但不論是什麼角色,他都是揮灑自如,而這些都成爲他在這裡說話的合格地位。
作爲學術、認真與關懷的人,邸立基贏得他讀者的信任。他在本書中向青年神學生所說的話,鮮有人可以帶有這樣厲害的話,而仍然是充滿恩惠與醫治。無疑在歐陸神學日新月異的領域中,鮮有比他更爲敏銳的神學家,在美國務實教會生活的廣闊道路上,可能有較他更爲能幹的行政人員,但鮮有人可以像他一樣將嚴謹綜合的學術研究結合於教會事工。這種綜合在今天的歐洲是特別需要,而我相信從另一角度來看,在西半球的一方亦是照樣受歡迎的。
邸立基教授生於一九〇八年,接受了傳統博大高深的德國神學教育。他於一九三〇年代經歷了一次個人危機,當時正值他的事業如日方中,但卻面臨著「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即納粹)的威嚇。他對納粹主義(Nazism)的反抗使他贏得了新的發言權,自從二次大戰以來,邸立基日益受人重視。毫無疑問,閱讀過本書而經驗豐富的神學家與教牧人員的書架上,一定會收藏了他的其他多本著述,反映了邸立基本人的廣泛興趣:《上帝與撒但之間》(Between God and Satan),《上帝的沉靜》(The Silence of God),《我們在天上的父》(Our Heavenly Father),《等待的慈父》(The Waiting Father),《世界如何開始》(How the World Began),《基督與生命的意義》(Christ and the Meaning of Life),《論虛無主義》(Nihilism),還有他對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德國新約神學家)的深邃回應。神學的初來者會很快地擁有與閱讀這些著述,並努力耕耘於他的龐大德文鉅著《倫理學》,或者是耐心地等待此書的英文翻譯(編者按:此書已譯成英文:Theological Ethics, 3 vol. set 1996, Fortress Press)。邸立基的寫作速度可以說是不下於我們的閱讀速度。
以上的生平概略並不是想藉此使讀者感到尷尬,而是想指出邸立基所具備的多種獨特優點是罕見的,並且是他所從事的,向人作出忠告的工作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神學對他來說是具備理論與道德的責任,你會看到他一方面定義神學爲「反省」(reflection),另一方面又形容它爲「意識」(conscience)。他的作品反映了內部的一致性,顯明邸立基的各種表述意義都是源自同一放射中心——就是反省與意識。
當然,作者的條件亦爲他的立論帶來不利的影響,他那過分強硬的作風有時蓋過了其他觀點的可能性。例如,他的基督徒意識過早壓倒了他在《論虛無主義》中所了解的虛無主義者。另外,他對比喻的解釋亦是教人感到詫異,然後當讀者參閱了經文及其他各種仔細對意義的探討後,例如耶尼米亞(Joachim Jeremias)與陶德(C. H. Dodd)等的著述,便可發現這些解釋可能較其忠於比喻的原意,邸立基的直觀與直覺是如此多姿多彩,以致一些意義與準確層面可能因此受損。
邸立基博士形容這書爲「神學小習作」(A Little Exercise for Theologians);其中是他在職責上爲自己學科開設的研討課。我認爲出版商有智慧地保留了本書的親切風格,他們保留了許多只是對原來聽眾,而不是美國的受眾有意義的地方,但因此我們卻好像親身聆聽了我們極希望親自出席的授課,這便使我們不會覺得是在接受一些無緣無故的忠告。邸立基稱這爲「習作」,在其心裡想著的是依格那修(Ignatius Loyola)的「屬靈操練」(Spiritual Exercise)及其他基督教自我修練的習作。我對此書有如下描述:這是一本有關神學上自我操練的課本,這可能只算是這博大領域的「小習作」;或可視爲一出《小夜曲》,或在壁畫底下留下的一些筆觸,但這卻在最微小的形式上可以顯明整體。在舞台劇中微音發出的提示可以間接顯明其他直接的台詞,這裡就是邸立基對神學聽眾的提示。
介紹書籍的人常常面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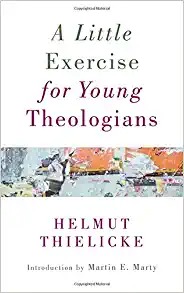 的誘惑,就是嘗試預測或重複書中內容,但我卻寧願與其論證對話。對於那些自覺正在或已經成爲神學家的美國基督徒來說,他們是否會同樣碰見本書所述及的問題?如其所述,歐陸的神學家,相對於其美國的夥伴來說,泰半活在象牙塔內;該處的活躍份子的積極性較低,那裡的神學不太關切教會的生活,只是關切嚴謹、科學與卓越的學術。在佈道、教會治理、牧養關懷、行政等方面,美國的教會都是遙遙領先的。
的誘惑,就是嘗試預測或重複書中內容,但我卻寧願與其論證對話。對於那些自覺正在或已經成爲神學家的美國基督徒來說,他們是否會同樣碰見本書所述及的問題?如其所述,歐陸的神學家,相對於其美國的夥伴來說,泰半活在象牙塔內;該處的活躍份子的積極性較低,那裡的神學不太關切教會的生活,只是關切嚴謹、科學與卓越的學術。在佈道、教會治理、牧養關懷、行政等方面,美國的教會都是遙遙領先的。
但傳統的圖畫正在不斷改變。德國神學家因著希特勒時代的衝擊,喚起了無比的勇氣,衝出他們的象牙塔,而他們亦不能再走回頭路,因爲在戰後宗教信仰如何適切世俗化世界的挑戰日益緊迫,與此同時,歐洲的教牧需要更努力的工作,才能獲得別人的重視,維繫與牧養他的羊群。
在美國,神學家在戰後亦有相同的任務,他是向「外人」,不單是向神學家說話。務實的教會工作者可能較其沒有經歷戰後宗教復興的歐洲同僚更爲駕輕就熟,這至少是從表面上來看。不過,在大西洋兩岸的神學家與教牧人員使命的差異,已經不是在本質上,而是在程度上而已,這樣的日子指日可待。
儘管上述的張力日漸鬆弛,神學的探索與行動的分享,與及支持它們的群體與個人之間的可悲鴻溝仍然存在。信徒會眾甚少承認或信任神學學問的價值,而神學學者亦甚少同情日日辛勞的牧者。基督教容許不同的恩賜,只是有同一聖靈,在同一群人中,我們會允許與鼓勵某些恩賜與才幹。邸立基便是在此論證每位耶穌基督的僕人都需要是自我操練的神學家與身體力行的教會工人。這是他的小習作的另一關懷。
除卻邸立基的大綱,我嘗試構想誰是神學在美國的敵人。首先是潛進教會圈子的普遍不信任氣氛,它規勸人迴避神學,其忠告是:基督教的信仰經不起智性的考驗,故此儘管忙碌吧,但不要分析與細察基督教的立場,這樣就可以生存下去。其次,一股冷漠感或短視正伸進教會的許多關鍵性的行動。只要不是馬上影響我教區範圍中教會四堵牆內的生活,我便不加理會。另外一個敵人就是將「行動家」(doer)加以偶像化,以之與「思想家」(thinker)相對立。那些能言善辯、長袖善舞的人總是較那些只會鑽研希臘文新約聖經的技工,能建起更多的房子,籌募更多的經費及宣講更響亮的講章。對某些人來說,他們毫不介懷其所做的會導致基督與生活意義、信仰與其他事物之間更大的割離,只要他的宣傳機器不停噴煙,他的佈道車輪運轉不停便心滿意足了。最後,我避免對此點言過其實,就是在美國宗教中存在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流傳於十九世紀對上帝敬虔與熱心的追尋,或是二十世紀因著相對主義衝擊下而產生的宗教副產品。
任何人若想在美國從事神學,按著邸立基的指引,他必須同情這些神學的敵人。上文所說互不信任的關係是大有道理的,首先是因著神學本身的限制而引起的不安,神學並不能時常解答一切問題,它不能解釋啓示沒有說明的事情,像「什麼是惡的本體來源?」等問題。另一些時候,理智所傾向的虛假答案亦常常叫人不能自己,自高自大。公元四世紀西西古斯(Cyzicus)主教優諾姆斯(Eunomius)曾言:「我認識上帝甚如上帝認識自己」,他許多時候似乎成了神學家的護守聖者。對普通基督徒與忙的不知其所以的教牧人員來說,將自己從教會生活與具體實況中抽離的傾向,可說是對基督教信仰的可悲誤解。事實上神學家知道更多與經驗更多時,便改變了他們的看法,這也會有時造成互不信任的情況,雖然事情不該如此,但我們不要忘記只有上帝才擁有完全的真理。毫無疑問,最常招惹批評的自然是神學家所特有的專業術語、暗語與隱語。我們欣然接受醫學上的專業術語(有誰喜歡被籠統的斷症爲「胃痛「?),或科學的專業名詞(連小孩子也能說出」洲際彈道飛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s missile」),但一旦關乎純淨福音時,我們卻對此絕不信任。邸立基在此點的忠告深具智慧。
不論神學的敵人是誰,或有任何導致彼此不信任的理由,教會卻應負起神學的必然任務,這便是我們的使命:盡「意」(或「心思」,mind)愛主你的上帝。世界正不斷轉變,新的問題不斷湧現,語言與意義上的基本探索層出不窮,難道我們要爲信仰建起細小的柵欄,或是高高的牆垣?還是信仰應面對廣大而繁複的世界?神學的任務具有內在的意涵:深入而淺出、承擔與見證。神學是無可避免的,問題它該是好抑是壞?有意識的抑是無意識的?自律的抑是鬆散的?
在美國處境中關心上述問題的,必會樂於看見邸立基教授這本忠告的英文翻譯。我們現在正面臨危機,就是信封大於賀卡,鬧哄哄的支撐著應該進行操練的場所。如何克服寫作過長引言的試探實在不易。屬靈操練需要人的回應、爭論與委身,若果它能在某些讀者的心靈中,不管他們是否神學家,或是否青年人,只要能喚起相同的誘惑,本書便可說是達到了其應有的目標。
本文係《神學第一步》(陳佐人譯,香港卓越書樓,1991)引言,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German Antidote Against America's Theological Ene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