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讀到關於蘇格蘭基督教的情況,這個國家的屬靈事實會讓你回想起大學青年團契的某個女孩——那個積極參加所有查經聚會的女孩,那個曾經計劃投身海外宣教的女孩。但現在,你讀到關於她的動態時會感到吃驚——她已經解構了她的信仰,比你想像的更徹底、更迅速。
她的轉折如此出人意料,以至於你可能會打電話給朋友,希望有人可以幫助你理解爲什麼會這樣。這甚至可能讓你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一些懷疑。
在過去,蘇格蘭的基督教——尤其是她對改革宗神學的堅持——一直非常堅強。蘇格蘭政府和教會都深受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的影響,而諾克斯又深受加爾文的影響。到20世紀20年代,蘇格蘭約有一半的人口都是教會成員(而且蘇格蘭幾乎所有教會都是長老會)。
在阿伯丁市(Aberdeen),有95座教堂爲當地18萬人提供服務。1965年,還是大學生來這裡進修的辛克萊·傅格森(Sinclair Ferguson)稱其爲「一座尖頂之城」。
他說:「這座城市看起來像現代的基督教雅典。到處都有教堂——也就是禮拜場所,教堂無處不在。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教堂都是由這種特別堅固、強大、幾乎壓倒一切的花崗岩構成。它們看起來真的很宏偉。」
蘇格蘭教會擁有一切:良好的神學遺產、高教會出席率和堅固的建築。它還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毫不干預。但是,如果你知道從哪裡觀察蘇格蘭教會,你會發現裂縫已經開始顯現。傅格森說,雖然教會成員眾多,但奉獻卻「很糟糕」。
不久之後,蘇格蘭的基督教就走向了崩潰。在60年裡,蘇格蘭教會成員從130萬驟降至30萬,同時聲稱沒有宗教信仰的蘇格蘭人的比例已經上升到近60%。
阿伯丁現在是蘇格蘭最世俗的城市,而蘇格蘭又是聯合王國最世俗的成員。巨大的花崗岩教堂建築成了餐廳、公寓,以及名字和「靈魂」一詞有關的酒吧。幾年前,一位記錄這種轉變的攝影師稱之爲「耶穌已經離開了教堂」("Jesus Has Left the Building")。

在阿伯丁市中心的皇后街,靠近警察局、市議會辦公室和當地媒體機構之地,坐落著該市最大的教堂建築之一。四年前,它被賣掉了——但這回不是賣給一家夜總會或零售店,而是賣給一個以福音爲中心的教會。
十多年前,三一教會(Trinity Church)已經脫離了蘇格蘭國教。在此後的幾年裡,她傳揚福音、開始了學生事工,並有了一些發展。對於這座巨大的建築來說,這間教會太小了,但當這間教會的成員們看著這個空間時,他們看到了可能性和盼望。
傅格森也是如此。他說:「若主許可,它將成爲這個城市的一個真正的燈塔。」
這些並不只是良好的願望而已。傅格森已經在阿伯丁買了房子。雖然已經退休,但這位有影響力的現代改革宗牧師-神學家將把他的主要時間花在蘇格蘭最世俗的馬路邊教會的晚堂講道上。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春天的標誌,」他說。「誰知道教會將看到什麼樣的收成?會是30倍嗎?60倍?還是100倍?那是神的事,也是祂的特權。但這個春天的跡象鼓勵我們繼續播種。」
最早在皇后街建造教堂的那間教會比三一教會早了大約165年離開蘇格蘭國教。他們的牧師約翰·慕里(John Murray)反對讓擁有土地的貴族(這些貴族不都是基督徒)決定這間地方教會的神職人員。他並不是唯一的反對者。在蘇格蘭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教會分裂中,1200名牧師中有474人退出了蘇格蘭國教,並於1843年成立了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
慕里帶領的這間教會後來被命名爲北區教會(the North Church),在一連串有影響力又有恩賜的福音派牧師帶領下,他們不斷壯大。到19世紀60年代初,該教會是「整個城市的福音中心」,教會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加米(Alexander Gammie)報告說。當這個宗派想開始向「城市的南部」拓展時,北區教會是帶領這場植堂的不二人選。
會眾「一致熱情地決定採用這一計劃」,加米在1909年寫道。爲了實現這一計劃,他們需要更多空間,因此他們建造了一座18500平方英尺的五層樓房。他們用傳福音活動、詩班和管絃樂隊來填充它。他們每週日舉行九次不同的聚會,然後在一週內再舉行26次。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在這個「工業蜂巢」周圍嗡嗡作響。加米寫道,他們做工的果效很明顯,以至於「許多參訪者從全國其他地方趕來觀看這個事工的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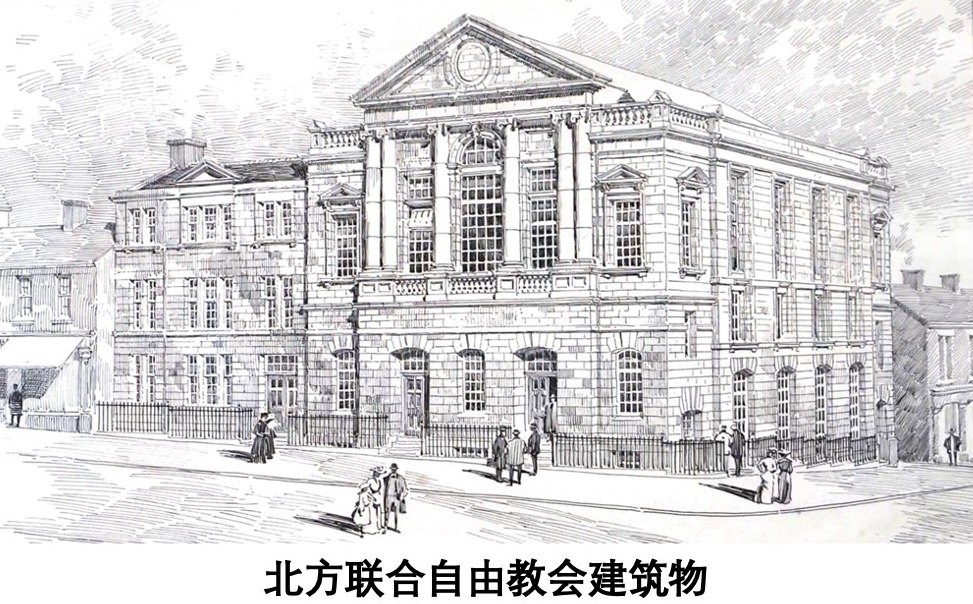
當時堪稱蘇格蘭教會的全盛時期,在那個時候,蘇格蘭是一個堅定地信奉改革宗神學的基督教國家,這個狀態持續了大約有350年。教義如此堅實,以至於很少有教會因爲神學而分裂。相反,他們一直在爭論誰可以任命牧師——是會眾還是上帝設立的政府。(也許你注意到查爾斯國王最近宣誓要維護蘇格蘭教會的獨立。而且,儘管他是英格蘭教會的官方元首,但他的這一地位並不延伸到蘇格蘭教會。這兩件事都不是偶然的。)
然而,當時也是牧師和神學家開始建議以新的方式來看待聖經的日子。這些神學家們說,聖經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這沒有關係。創世故事可能是巴比倫神話,亞伯拉罕實際上並不存在,挪亞時期的洪水幾乎肯定沒有發生,也不存在吞掉約拿的魚。實際上這些神學家認爲,《舊約》顯示了人類的宗教演變,表明人類如何擺脫了那些原始的信仰。
「到了歷史的這一刻,基督徒的基本問題是:『上帝的話語說了什麼?』」真理旌旗(Banner of Truth)出版社的編輯伊恩·默里寫道。「新的問題變成了:《聖經》中有多少是神的話語?」
下一個問題很自然地成了:「那基督呢?他所說的有多少是真的?」
教會「失去了信心,迷失了方向。」教會長老西蒙·巴克(Simon Barker)說,在過去幾十年裡,他看到這種情況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都在持續發生。教會「突然爲基督感到羞愧,認爲教會不可能指望人們相信復活的救主。因此,帶著一種啓蒙的態度,相當尷尬地盯著自己的腳,停止教導教義,開始說:好吧,只要我們對鄰舍和善,經常和鄰舍打球,我們就會有好見證。」
1929年,當曾經脫離國教的蘇格蘭自由教會中大部分決定重新回歸蘇格蘭國教時,他們做出了一個妥協性的聲明——上帝的話語「包含」在聖經中。宣揚聖經有謬誤的神學家沒有一個受到懲戒。
當傅格森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獲得神學學位時,他的教授中只有一兩位是傳統福音派人士。福音派的學生俱樂部規模很小,他們開玩笑說他們可以在電話亭裡開會。
然而,四百年來的優秀神學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與教會有關,」傅格森說,儘管他的父母沒有參加任何聚會,但他每週都去上主日學。在國家開辦的學校裡,他記住了十誡、主禱文和天國八福。教會的禮拜有電視轉播,雙層巴士會帶著孩子們參加主日學野餐,全國媒體會廣泛報導每年的大會。
但奉獻開始下降。你可以在《蘇格蘭教會年鑑》中查到,該年鑑將蘇格蘭每個教會的人數和年奉獻額放在一個表格裡進行統計。
傅格森說:「當我在大學圖書館時,我無意中聽到一位牧師和學院圖書館管理員之間的對話。那位牧師說,『你看到斯蒂爾先生(Mr. Still)所在教會的驚人奉獻了嗎?」
傅格森的耳朵聽到了這句話——他是斯蒂爾通過解經式講道和對主的愛所振興教會的一部分。(想聽更多關於這個故事的內容,請聽傅格森的音頻故事。)
「圖書管理員說,『哦,是的,雖然他的教會裡都是學生。』」傅格森回憶說。那位圖書管理員的回答似乎沒有解釋教會爲什麼有那麼高的奉獻收入。「學生沒有很多錢,」他想,「那是胡說八道。」
人們不奉獻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不去教會。儘管在1957年約有60%的蘇格蘭人是教會成員,但每週去教會的人不到20%。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長長的教會成員名單掩蓋了這個問題。這也扼殺了傳福音的動力。
「這讓我們這些福音的執事感到滿意,好像我們在蘇格蘭的傳福音責任已經完成一半了。」湯姆·艾倫(Tom Allan)寫道,他是1955年葛培理蘇格蘭佈道會的執行主席。
一些篤信聖經的基督徒採取了行動——爲期六週的葛培理佈道會讓數千人接受了基督。20世紀70年代初,威廉·斯蒂爾開始邀請牧師們參加聚會。這一活動後來發展到每年幾百名福音派牧師——這是蘇格蘭國教大會之外最大的會議。在傅格森的校園團契小組中,任何不解經的人都不會再來了。更多的人進入牧師行列,不是因爲他們的父親,而是因爲他們感到了蒙召。
傅格森說:「這增加了上帝在我們這個時代做事的感覺。風就在我們背後。」
傅格森說,雖然有福音派牧師和一些福音派教會成員,但他們即使在自己的會眾中也通常是少數。因爲「除非福音以社區爲基礎,否則無法保證其未來。」
也沒有什麼架構來支持他們。他說:「在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創建了一些機構。我不是貶義的意思,而是一種稱讚。福音派機構讓福音派信念得到了制度化的保存,這樣就可以傳遞下去、服事未來。」
在蘇格蘭,人們不會如此迅速或輕易地撰寫一份聲明或創建一個非營利組織。
他說:「(蘇格蘭福音派領袖們的)策略——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策略——基本上就是沒有策略。他們常用的說法是『悄悄滲透』。」
在一間教會裡,一個保守的牧師有時可以做到這一點。但在宗派層面而言,這樣做並不奏效。相反,溫和的中間派——即便他們都是相信耶穌的人——選擇了阻力最小的道路。在一個自由化的文化中,這一策略的結果就是自由化。
傅格森說,「悄悄滲透的危險在於,最後是自己被悄悄滲透了。」
這就是由高舉科學、理性的文化所滋養的聖經有謬誤這一涓涓細流如何能發展成了溪流。這就是在一個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真理這種文化滋養下,在聖經無誤上妥協的小溪如何最後變成了大河。
漸漸地,這種運動可以沖垮一個教會的根基——一個400年來堅持以改革宗神學爲基礎的厚實根基。
在20世紀六十年代的某個時候,教會垮了。
牧師大衛·蘭德爾(David Randall)在2015年寫道:「多年來,教會的衰落被歸咎於『枯枝落下』,即那些成爲教會成員卻沒有對基督作出任何真正承諾的人離開了教會。他們的離開讓教會變得更結實、更健康的教會,這一想法一度讓我們感到安慰。」
這種安慰並沒有持續多久。在過去的六十年裡,蘇格蘭的教會成員人數沒有出現反彈、上漲,甚至也沒有減緩直線下降的趨勢。
官方的說法是,教會因蘇格蘭的出生率下降或教會未能接觸到年輕一代而受到影響,更好的技術使用或更多的自由化可能會有所幫助。自2009年以來,蘇格蘭國教一次又一次地投票,以擴大對同性關係的認同。
這些投票非但沒有吸引教會以外的人來到教會,反而只是加速了保守派牧師候選人、牧師和教會的出走。
其中一個是阿伯丁北側的希爾頓高地教會(High Church, Hilton)。
90年代中期,彼得·迪克森(Peter Dickson)悄悄地在希爾頓高地開始了福音派事工。
大衛·吉布森(David Gibson)說,「他有效地在一個瀕臨死亡的教會中植入了福音,」大衛後來成了彼得的助理牧師。「他們沒有聆聽聖經教導的基礎,所以迪克森從10分鐘的講道開始。」
每隔一段時間,迪克森就會延長講道時間,直到最後達到30分鐘。
吉布森說:「他用解經式講道餵養著教會中的男女,愛他們,以及通過使自己的家成爲一個歡迎和關懷的地方而得到改變。他慢慢地提高了教會生活中的屬靈溫度。」
西蒙·巴克是長老議會的一員,他說:「我不認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真的信主,因此看著他們真正信主是一種謙卑下來的經歷,」他說。「我經歷這種謙卑好幾次。」
在迪克森服事大約15年後,同一個長老區會下面的另一間教會呼召了一位離開妻子和女兒參與同性關係的男士擔任牧師。迪克森和其他11位牧師表示反對,在當地長老區會和後來的全國總會上爭論不休,並最終失敗。
經過三年的「談判、討論、教會法庭、決策和通信」,蘇格蘭國教決定差派一位長老前來「評估」和幫助治理希爾頓高地教會。對此,迪克森的回應則是離開了國教。
「15年前,沒有人會和他一起離開,」吉布森說。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會眾已經定期聽到福音多年了。在200多名成員中,有170人隨他而去。
他們是第一個因蘇格蘭國教在同性議題上的立場而離開該宗派的教徒。
巴克說:「那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他一直都是蘇格蘭長老會(國教)的一員。把福音放在你的宗派委身之前,特別是如果你是第一個離開的人,這是非常痛苦和疲憊的。
「我們爲之哭泣,」他說。「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從來不想分開——那會向世界發出什麼樣的信息?這並不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出走的這個團體自稱「三一教會」,並開始在一個褪色的藝術裝飾酒店宴會廳聚會,在那裡你有時可以找到派對的殘留物,或聞到前一天晚上的酒味。
巴克說:「這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讓我們知道不要依賴建築物。但它也教會了我們,沒有建築物的教會運作是多麼的有限。」
「三一教會」在聖誕節和復活節時無法租到場地,因爲大型派對預定了所有的場地。沒有固定的地方,也就意味著他們很難邀請朋友參加聚會,也很難開始鄰里事工。而且他們總是意識到,某些講道片段一旦得到病毒式傳播,就會讓他們失去場地。

這種無根的感覺因爲加入了國際長老會(IPC)作爲他們的新長老會家園而變得更加複雜。IPC由薛華(Francis Schaeffer)創立——想想看,應當帶來很多好的對話、很多好的團契,而且近年來在英國和歐洲有令人興奮的教會植堂活動。這裡有對認信的委身和以福音爲中心的教會生活。但關係是新的,需要時間來深入發展。
迪克森和吉布森不斷地需要講道,一個星期天接著一個星期天。最後,迪克森轉而帶領蘇格蘭大學和學院基督教團契(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的學生事工,而吉布森則開始擔任三一教會的主任牧師。
吉布森說:「彼得在希爾頓和三一的事工所付出的代價和非同尋常的忠心,以及他的長期成果,是我所看到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慢慢地,三一教會繼續成長。他們開始爲自己的建築籌集資金。在一次IPC會議上,吉布森認識了辛克萊·傅格森,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改革宗神學家之一。
傅格森也因此認識了大衛·吉布森。
「上帝給了大衛一個巨大的決心,」傅格森說。「他智識超群,而且他是一個非常有恩賜的解經者。他對會眾有一種真正的愛。而且與他的長老們一起,他們有一種真正的熱情,即他們可以在這個城市創造一些東西。」
還記得1843年離開蘇格蘭國教的教會嗎——由約翰·慕理帶領的教會?那個有如此多的聚會、事工和志願者的教會,以至於當時許多觀察家稱這間教會是一個「蜂巢」。
在最近的100年裡,這個蜂巢幾乎是空的。只有30名年紀老邁的成員在龐大的建築裡緩慢移動,這座建築物擁有一個能容納1000人的主堂,另外兩個大廳、多個教室,以及讓管理員居住的三居室公寓。

1929年,該教會重新加入了蘇格蘭國教,隨後就面臨著人數下滑,雖然該教會在成員人數減少的情況下一直在有效地整合資源。
因此,日漸萎縮的前北區聯合自由教會在2004年與附近的教會合併,並在2017年再次合併。甚至在蘇格蘭國教正式批准同性婚姻之前,該教會就「決定放棄蘇格蘭教會在人類性行爲方面的傳統立場,以實現包容性」——這段話引自教會網站上的自我介紹。
然而,因爲人數太少,到了今年5月,蘇格蘭國教宣佈它將在未來5年內關閉這間教會。
就在三一教會有足夠的資金認真考慮購買會址的時候,北區教會的這座老建築進入了房地產市場。由於該建築仍然屬於會眾——因爲1929年的文書工作出了錯——三一教會可以在不需要蘇格蘭國教介入的情況下購買它。
「我記得當時有點怕,因爲它太大了,而且裡面有很多房間,」巴克說。它也需要許多更新和維修。屋頂漏水、電力系統需要大修,每個房間都需要進行一些改造。
「你們可能只想買一部分,」賣家代表建議三一教會的長老們。
但他們越看越興奮。
吉布森說:「它好像呼籲我們讓它成爲位於市中心的一個福音中心。他可以想像著在這裡爲企業高管提供福音午餐會,爲無家可歸者提供食物或庇護所的事工,以及在管理員公寓裡安置教牧實習生。」
這是一個美麗的願景。但這將需要大量的工作,如果能得到一些幫助就更好了。
寫了50多本書,在幾乎所有的改革宗大會上講道,在幾乎所有的改革宗神學院任過教,以及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個歷史悠久的教會擔任過牧師……這是一份令自己滿意的履歷,傅格森於2013年退休。
除了爲他的繼任者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帶領騰出空間外,他沒有其他的退休安排,因此回到了蘇格蘭的家。他在女兒的教會幫助了一段時間。當她的牧師在2019年搬到澳大利亞時,傅格森知道他想給新的主任牧師一些喘息空間。
在IPC的一次活動中,他提到了自己目前的安排。
吉布森聽到了。他回家後寫了一封信,邀請傅格森加入三一教會在阿伯丁的工作。
18個月過去了,吉布森沒有收到任何答覆。新冠疫情來了,三一教會的聚會轉移到了網上,他們變得更忙了。
「然後有一天,我在一家超市裡,他打電話來,」吉布森說。傅格森當時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上。(如果他不去做牧師的話,職業高爾夫是他可能採取的路線。)
「我很感興趣,」傅格森告訴吉布森。「我們來談一談。」
傅格森很好奇,就提出想要來看看這座教堂,在疫情期間,三一教會曾使用過這座教堂,但在修復之前又搬了出來。傅格森第一次走進去的時候,他感到「目瞪口呆」,他說:「這座教堂很有潛力。」他知道教會不是建築物,但他喜歡在阿伯丁的中心地帶建立一個繁榮、活躍、熱鬧的強大神學和事工中心這一想法。
傅格森說:「就像一本書的封面一樣,建築物確實能說明一些問題。如果上帝賜予供應,並且(三一)實現了它,那麼它就能成爲一個很好的見證,表明這裡正在發生一些事情。……人們可能會想,『爲什麼在其他教會關閉的時候,這個教會卻在擴張?』」
即使你所在的教會信仰告白是約翰·諾克斯寫的,即便教會的神學扎根於《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即便你的建築是由花崗岩製成的,如果沒有福音,你的教會仍然會失敗。
巴克說:「在我們這個城市裡,基督教的精神幾乎消失了。那些在我們之前的人忠心耿耿地服事,建立了教會,而我們卻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揮霍了它。這是很可怕的。」
傅格森說:「那些曾爲福音提供最大機會的地方,當他們不再需要福音時,就會變成非常艱難的地方。幾年後,阿伯丁的市中心將只有四個蘇格蘭國教教會。」

吉布森說:「在城市的這一部分,沒有活生生的福音見證。三一教會的這座建築物正好位於該市的市民、經濟和司法中心——街邊有商業,拐角處有法院,隔壁是城市規劃的商店和廣場。阿伯丁大學也在步行範圍內。」
這個位置很適合建立教會。但植堂必須盡快發生,吉布森說:
「如果三一的事工有任何成果,那都是來自於之前幾年流淚播種的東西。我們經常使用『植堂』這種機構化語言,但很少注意到基本的種子原則,即種子埋進土裡死了,植物才能長出來。彼得的忠心和帶領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帶領我們進入新的領域,我們在其中耕耘和播種。而三一教會現在只是想繼續進行同樣昂貴的事工。已經有很多人死去了!……我不認爲任何做這些事的人從未質疑過——這值得嗎?但我們相信它是值得的,正是因爲我們已經嚐到了死在地裡的種子帶來的果實。」
在招募傅格森的同時,吉布森一直在講道,希望更多的奉獻者可以爲教堂重修工程捐款,並幫助計劃蘇格蘭版的查爾斯·西緬釋經工作坊。到明年9月,一個小型的牧師聯盟將提供課程,包括解經原則、敘事文講道和福音事工方法論。他們將在三一教堂的新空間裡舉行會議。
像他之前的那些人一樣,吉布森想把福音傳到未來。而且他想在從過去的改革宗基督徒那裡得到的建築中做到這一點。
「我把它看作是一個巨大盼望的標誌,」傅格森說。「有這些春天的跡象。你知道,主不需要給我們這些春天的跡象,但他就是給了。而三一教會肯定是其中之一。」
編注:要了解辛克萊·傅格森的更多故事,請聽「爲什麼辛克萊·傅格森搬回蘇格蘭最世俗的城市」播客,想了解更多關於三一教堂和阿伯丁的情況,不要錯過這個10分鐘視頻。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Jesus Has Left the Building': Scotland's Secular Slide—and Signs of H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