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喬治·弗洛伊德去世後的幾個夜晚,明尼阿波利斯市大湖街(Lake Street)一帶的天空一直都火光沖天。
騷亂者燒燬了一家4S店(AutoZone)、一家手機店和一家餐廳(Town Talk Diner)。第二天晚上,他們破壞了一家人事代理公司、一家賽百味(Subway)和一家富國銀行(Wells Fargo)儲蓄所。僅僅72個小時,暴徒們打碎了玻璃,偷走了商品,並放火燒燬了數百家商店。
在大湖街往北兩英里就是74歲老牧師約翰·派博的家,他可以看到升騰的黑煙,他像往常一樣上床睡覺。
 「我睡的還可以。」他這樣告訴福音聯盟。幾乎沒有什麼能讓他和他的妻子諾爾(Noël)感到害怕,他們自1980年以來一直住在這個資源不足的社區中,一棟簡陋的房子裡。他們知道如果聽到槍聲該怎麼做(打911,然後看看自己能不能幫上忙),如何清理前廊上的十幾根吸毒者遺棄的皮下注射針頭(用掃帚掃起來,不碰它們),以及如何嚇退闖入你家的人(開門大喊)。
「我睡的還可以。」他這樣告訴福音聯盟。幾乎沒有什麼能讓他和他的妻子諾爾(Noël)感到害怕,他們自1980年以來一直住在這個資源不足的社區中,一棟簡陋的房子裡。他們知道如果聽到槍聲該怎麼做(打911,然後看看自己能不能幫上忙),如何清理前廊上的十幾根吸毒者遺棄的皮下注射針頭(用掃帚掃起來,不碰它們),以及如何嚇退闖入你家的人(開門大喊)。
派博四十年前搬進來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復興城市文明的宏偉願景。他只是希望能步行上班,並認爲住在教會所在的社區能讓服事更真實。不久後,他堅信「存在於社區中對福音見證很重要」,於是發出號召,讓伯利恆教會的成員加入他的行列。十年之內,這間教會中的400人在這個城市最糟糕的地區之一買了房子。
 那是1980年的事了,那時生活在城市一點都不酷,遠在2012年提摩太·凱勒出版《21世紀教會成長學》(Center Church)或2015年美南浸信會將「差派網絡」(Send Network)的新教會植堂以城市爲目標之前。在那時候,教會搬到郊區會有意義——離大多數成員更近、有更多發展空間——但伯利恆浸信會還是留在市中心。
那是1980年的事了,那時生活在城市一點都不酷,遠在2012年提摩太·凱勒出版《21世紀教會成長學》(Center Church)或2015年美南浸信會將「差派網絡」(Send Network)的新教會植堂以城市爲目標之前。在那時候,教會搬到郊區會有意義——離大多數成員更近、有更多發展空間——但伯利恆浸信會還是留在市中心。
「城市需要教會,」派博說,「我們不應該因爲經濟原因而放棄城市。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教會已經在這裡待了111年。神把我們放在這裡。如果我們走了,市中心這邊就會失去一個福音派教會,更何況已經所剩無幾了。」
派博教會的成員們在沒有總體計劃的情況下就搬進了城市,這既讓人困惑(「我們應該怎麼做?」),但同時恰好是《當幫助帶來傷害時》(When Helping Hurts)一書作者後來的建議(從建立關係、觀察和學習開始)。
每個人最後都做了不同的事情。但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堅持,在失望和挑戰、搶劫和騷亂、破碎的玻璃和公園裡無家可歸的帳篷城中努力。他們至今仍然在這樣服事。
隨著喬治·弗洛伊德遇害的消息傳開,塔吉特百貨(Target)員工就開始收到公司短信,告訴他們不要進城上班。其中一位員工是牧師約翰·埃里克森的兒子,他們家就住在派博家對面。
「我當時就想,『這是怎麼回事?』」 埃里克森說,「然後我意識到搶劫已經開始了。週二到週三,這個城市變得毫無生氣。週二、週三、週四都沒有警察的存在,也沒有消防的存在。我於是對教會的領袖們說,『我們得做點兒什麼。』」
 埃里克森幾乎一輩子都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他的父母在1982年聽到民權活動家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談到搬遷到破碎地區的重要性後,就主動搬到了菲利普斯社區(Phillips)。雖然當時與派博住的地方只相隔六個街區,但埃里克森直到在加州讀馬斯特斯大學(恩典社區教會所辦的大學)時才碰到派博,他形容當時的派博是個「野心勃勃的激進分子」,在大學的禮堂裡講道。埃里克森後來加入了伯利恆浸信會成爲職員和牧師長達十年,在三年內植堂建立了兩間教會。
埃里克森幾乎一輩子都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他的父母在1982年聽到民權活動家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談到搬遷到破碎地區的重要性後,就主動搬到了菲利普斯社區(Phillips)。雖然當時與派博住的地方只相隔六個街區,但埃里克森直到在加州讀馬斯特斯大學(恩典社區教會所辦的大學)時才碰到派博,他形容當時的派博是個「野心勃勃的激進分子」,在大學的禮堂裡講道。埃里克森後來加入了伯利恆浸信會成爲職員和牧師長達十年,在三年內植堂建立了兩間教會。
他現在仍然帶領著第二家教會,禧年社區教會(Jubilee Community Church),這間教會就位於伯利恆浸信會以南不到三英里的地方,距離弗洛伊德遇害的地方僅一英里之遙。自2009年創立到如今,這間教會已經發展到175名成員,成員們像埃里克森一樣深入到附近社區服事。例如,當他注意到周邊社區沒有少棒隊——因爲很多孩子都沒有父親,這就意味著缺乏教練——他開始了菲利普斯火蟻隊。
在發生騷亂後的第三個晚上,「我們去了Target超市停車場,在那裡搭起了一個禱告帳篷,」埃里克森說。當他問警察是否可以這樣做時,得到的答案是:「這是一個戰區。隨你們……這可能會帶來好處,但我們無法保護你們。」
因此,當人們闖入Target超市,搶劫了他兒子本來要進貨和清點的商品時,埃里克森和他的教會分發瓶裝水並邀請人們一起禱告。「我們和很多很多人進入了交談,」他說,「我們教會的人開始來了。人們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這裡,幫忙清理。但你能感覺到空氣中的氣氛很不穩定。我們知道——夥計,這必定會是個不眠之夜。」

的確是個不眠之夜。在禧年教會成員收拾東西離開後不久,有人在離他們原先站立的地方幾英尺遠的地方燒燬了一輛汽車,另一個人被刺傷。第三分局警署遭到佔領和摧毀。
第二天晚上,埃里克森把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送回娘家,而他和大兒子則在家裡觀察和祈禱。他們拿出了花園裡的水管,以防火勢蔓延到他們的街區。埃里克森接到教會成員的電話,他們的問題都是類似於這樣的:「我的街區著火了,消防隊不來了,我該怎麼辦?我想我需要疏散離開,但外面有太多人,我沒法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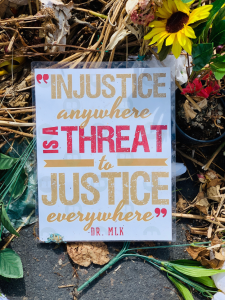 但即使是那些前往城外的家人或朋友那裡避難的人,也在一兩天內回來了。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來自許多教會的基督徒一同清理碎玻璃,進行行走禱告,並在「耶利哥之路」——一個在禧年教會地下室向鄰居提供食物和社會服務的組織——做志願者。
但即使是那些前往城外的家人或朋友那裡避難的人,也在一兩天內回來了。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來自許多教會的基督徒一同清理碎玻璃,進行行走禱告,並在「耶利哥之路」——一個在禧年教會地下室向鄰居提供食物和社會服務的組織——做志願者。
「我們覺得應該長期在這裡,倍增門徒,」埃里克森說,「我們希望看到人們真正長期與耶穌同行,看到健康的教會建立起來。」
這意味著「在附近忠心耿耿,只是蹣跚前行,」他說,「每一天你都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大成就。只是一點一滴,主在幫助我們。」
騷亂發生的當晚,在完成了一整天的服事後,傑夫·諾伊德正在修剪他的灌木。
這並不是說他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冷漠無情——他能感覺到附近「壓力越來越大」,就像「一個準備爆炸的火藥桶」。他住在離大湖街三個街區的地方,他能看到黑煙,聽到交火的槍聲。
 「我真的希望晚上能和其他牧師一起在第三分局門口祈禱。」他說,但諾伊德的服事對象是那些資源不足的人,新冠疫情給這些人帶來了很多艱難。他日夜不停地工作已經好幾個月了,甚至很多週末都得擺上,他已經筋疲力盡了。
「我真的希望晚上能和其他牧師一起在第三分局門口祈禱。」他說,但諾伊德的服事對象是那些資源不足的人,新冠疫情給這些人帶來了很多艱難。他日夜不停地工作已經好幾個月了,甚至很多週末都得擺上,他已經筋疲力盡了。
因此,他只是把垃圾桶拉到車庫里,這樣就沒人能在裡面點火了。然後他做了一些不用動腦的體力勞動,這樣他就可以放鬆他的大腦。
他修剪了他的灌木,因爲它們長得有點太高了,而且也是因爲他住在這個社區,並且打算長住。
諾伊德從1985年開始就一直住在菲利普斯,當時伯利恆開辦了一個團契小屋(名爲「koinonia」,希臘文「團契」之意),讓年輕人住在一起,同時在這個社區傳講福音。
 然後他認識了一個女孩,與她結婚了,在附近買了一套房子。然後,他只花了一美元就買下了旁邊的房子,修繕了一下,租了出去。然後,他又結識了馬路對面的鄰居——他們是從卡特里娜颶風中撤離的人——甚至帶著他們的孩子去邊界水域(The Boundary Water)划獨木舟。他看著這些孩子們歸向了基督,僅此一個收穫就讓他願意再做一次。
然後他認識了一個女孩,與她結婚了,在附近買了一套房子。然後,他只花了一美元就買下了旁邊的房子,修繕了一下,租了出去。然後,他又結識了馬路對面的鄰居——他們是從卡特里娜颶風中撤離的人——甚至帶著他們的孩子去邊界水域(The Boundary Water)划獨木舟。他看著這些孩子們歸向了基督,僅此一個收穫就讓他願意再做一次。
諾伊德從事城市中心貧民區事工已經28年了。他帶領著「耶利哥之路」,這事工是在禧年教會的設施裡運作的。他和兩名助手(以及大約30名志願者)將人們與社會服務機構聯繫起來,幫助提供簡歷和國家身份證明,協助處理財務危機,並分發食物。即使在騷亂之前,新冠疫情就已經把2020年變成了異常具有挑戰性的一年。
「3月份,我們分發了5萬磅食物,」諾伊德說,「4月份,我們做了10.8萬磅。5月,我們做了12.8萬磅。」
當騷亂破壞了附近的雜貨店後,「耶利哥之路」就在大湖街設立了食品貨架供應有需要的人。現在,諾伊德和他的志願者們正在努力解決下一個問題——向無家可歸者在附近公園裡搭建的數百頂帳篷發放水和衛生用品,因爲6月份市政府宣佈這些帳篷爲避難場所。
 「一些(帳篷住戶)是從城外來抗議的,然後留了下來,」諾伊德說,「有些人來自美國原住民保留地,把這看作是一個找工作和重新安置的機會。」他希望參與爲他們尋找住房資源的服事。他們可住的地方之一是由前伯利恆教會成員、現在某個家庭教會成員吉姆·布魯姆和塞西爾·史密斯購買並經營的綜合公寓。(「他們服事附近最貧困的人,他們是按著國度價值觀在進行管理,」他們的朋友拉斯·格雷格說,「多年來,他們已經服侍了數百人。」)
「一些(帳篷住戶)是從城外來抗議的,然後留了下來,」諾伊德說,「有些人來自美國原住民保留地,把這看作是一個找工作和重新安置的機會。」他希望參與爲他們尋找住房資源的服事。他們可住的地方之一是由前伯利恆教會成員、現在某個家庭教會成員吉姆·布魯姆和塞西爾·史密斯購買並經營的綜合公寓。(「他們服事附近最貧困的人,他們是按著國度價值觀在進行管理,」他們的朋友拉斯·格雷格說,「多年來,他們已經服侍了數百人。」)
諾伊德還記得幾十年前,當他告訴父親他要搬進菲利普斯時,來自父親的懷疑和反對。他的父親並不反對幫助他人,但認爲諾伊德可以仍然住在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然後去幫助他人。
諾伊德承認,這樣想也沒錯,他本可以這樣做。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但與你服事的人住在同一個社區會給你一個獨特的見識,」他說,「你就有機會參與街區俱樂部、參與週間查經,有機會看到槍擊案、謀殺案和被盜的車輛。」
還可以看到警察的不公正、騷亂和無家可歸者的帳篷城,看到人們來到基督面前,看到人們獲得足夠的食物養活他們的家人,並最後在經濟上自立。
「的確有困難的日子,相信我,」他說,「但總的來說,我會用這個詞來描述這裡的事工:這樣的服事是一種特權。」
騷亂發生的當晚,拉斯·格雷格哭了。
「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悲傷的一天,」他說,「我們在這裡生活了30年,看到城市的發展在一瞬間被摧毀,這著實令人心痛。」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菲利普斯一直在慢慢改善。在經歷了60、70、80年代的白人逃離城市之後,伯利恆浸信會成員和其他人士的存在幫助穩定了這個社區。與此同時,廉價的住房吸引了難民——尤其是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逃離東非戰爭的難民,城市願景(City Vision)的執行總監約翰·梅爾(John Mayer)說:「基本上是移民們重建了這個社區,是基督徒開始禱告和傳福音,並關心人們。」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菲利普斯一直在慢慢改善。在經歷了60、70、80年代的白人逃離城市之後,伯利恆浸信會成員和其他人士的存在幫助穩定了這個社區。與此同時,廉價的住房吸引了難民——尤其是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逃離東非戰爭的難民,城市願景(City Vision)的執行總監約翰·梅爾(John Mayer)說:「基本上是移民們重建了這個社區,是基督徒開始禱告和傳福音,並關心人們。」
今天,菲利普斯街頭有100多種語言——最常見的是西班牙語和索馬里語。各個族群的商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2006年,一座巨大廢棄的西爾斯大廈被重新啓用。現在這裡是Alina Health公司總部、中城全球市場和住宅區的所在地。這裡也是大部分騷亂發生的地方,全球市場的幾十家企業被毀。
「就在我們的城市在騷亂中被摧毀的那個晚上,我們爲高中畢業生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晚宴。」格雷格說。他20年前開始了這所學校,因爲當時他聽了派博講道,說要爲上帝冒險做一些『有點瘋狂』的事情。第二天,格雷格辭去了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最富有的郊區一所基督教學校發展總監的工作,在菲利普斯創辦了一所基督教經典教育學校。
 二十年後,希望書院從教會地下一層35名學生發展到七層教學樓的500名學生。在這個有色人種兒童畢業率全美最差的地區,希望學院的學生學習莎士比亞,操練美德,並獲得大學獎學金。
二十年後,希望書院從教會地下一層35名學生發展到七層教學樓的500名學生。在這個有色人種兒童畢業率全美最差的地區,希望學院的學生學習莎士比亞,操練美德,並獲得大學獎學金。
「培養具有學術資格——但更多的是內心資格——僕人領袖對我們城市來說至關重要,」格雷格說。
當他們的社區遭到破碎和燃燒時,希望書院2020屆畢業生在Zoom上聚會、慶祝他們的畢業,並聽取他們每一位老師的致辭。每一位老師都在最後們告訴他們:「希望書院與你們的家人約定,要培養你們成爲一個國度的公民。現在是你們爲社會正義和經濟發展、種族和諧和喜樂合作而努力的時候了。請記住,耶穌來不是爲了受人服事,而是爲了服事人。」
「我們聽到這句話21次,」格雷格說,「當我們禱告時,我們都在想,我們的城市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未來的領袖。那是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過去五個月的全球疫情、經濟不確定性、種族不公和騷亂,會讓人覺得上帝已經拋棄了菲利普斯。
 「但神沒有。」格雷格說,「而且他甚至可能策劃了這一切,以實現他國度的目的。」格雷格已經可以瞥見這一點——他的老師們與學生家庭的接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定期打電話詢問情況。他們給一些人送去了雜貨,花錢更換了另一個人的破冰箱,提供了硬幣讓另一個人可以使用洗衣店(因爲通常提供硬幣兌換的銀行已經被砸爛了)。希望書院還設立了一個新冠疫情救濟基金,幫助家庭解決學費問題,收到了近10萬美元的捐贈。
「但神沒有。」格雷格說,「而且他甚至可能策劃了這一切,以實現他國度的目的。」格雷格已經可以瞥見這一點——他的老師們與學生家庭的接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定期打電話詢問情況。他們給一些人送去了雜貨,花錢更換了另一個人的破冰箱,提供了硬幣讓另一個人可以使用洗衣店(因爲通常提供硬幣兌換的銀行已經被砸爛了)。希望書院還設立了一個新冠疫情救濟基金,幫助家庭解決學費問題,收到了近10萬美元的捐贈。
接下來格雷格會努力給市議會成員打電話,介紹帳篷城的情況。營地裡的骯髒注射器、性侵犯和暴力意味著菲利普斯的孩子們不能在公園裡玩耍。自7月以來,大多數帳篷已經被拆除了。
「在我們街區盡頭,有30個帳篷在一塊空地上。希望書院旁邊的公園裡還有10到12個帳篷。」格雷格說,「前幾週,一個18歲的孩子在那個公園裡被槍殺了。感覺我們就像生活在一個戰區。」
但格雷格留了下來,因爲他知道這是一場只能以一種方式結束的戰爭。
「神必然得勝,」他說,「國度必然得勝。我所做的是充滿希望的冒險,愛是我這樣做的理由。……在接下來的四到五個月裡,看到神如何使用他在這裡安插的子民去愛、去服侍、去以重要的方式帶領,這將是很有趣的。」
火災發生的那晚,佟明璟並不在菲利普斯。雖然他在那裡住了十年,後來搬到了城北的另一個社區。
但身爲伯利恆社區福音拓展牧師的佟明璟,第二天一早就出現在了菲利普斯。
 有朋友給他打電話,問他要不要和他家一起撿碎玻璃。「我就在Facebook上發起了一個活動,主要只是在自己的頁面上分享給附近的人。」他說,「一個小時內,我的活動就得到了1200次分享。這真是太瘋狂了。」
有朋友給他打電話,問他要不要和他家一起撿碎玻璃。「我就在Facebook上發起了一個活動,主要只是在自己的頁面上分享給附近的人。」他說,「一個小時內,我的活動就得到了1200次分享。這真是太瘋狂了。」
一小時後,當他見到他的朋友時,又有400人來參與了。
「這只是來自(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雙城附近的人,」他說,「我不知道他們是誰。所以我們做了一堆清理工作。因爲我做了10年的街區清理工作,我知道該怎麼做。」(包括了打電話給存放手套和袋子的五金店老闆,向市政府索要黃色垃圾袋——這表示垃圾已經被志願者收集起來,垃圾車將免費收集。將裝滿的袋子堆放在路邊。)
第二天早上,暴動帶來的破壞更加嚴重,而且從大湖街蔓延到更遠的地方。明璟和他的朋友尼克·斯特羅姆崴(Nick Stromwall)去了教會,並建立了一個「支持城市」的網頁。
「我們基本上是說:我們做這個網頁是爲了幫助人們知道損失在哪裡,需求在哪裡,以及你可以去哪裡獲得幫助,」 明璟說,「在五天之內,我們有近22000名追隨者。從Facebook的統計數據來看,我想我們動員了大約8000人參加我們創建的30個活動。」(他們還推廣了其他人發起的活動。)
 「支持城市」之所以廣受歡迎是因爲它正好填補了一個需求。但佟牧師之所以能如此靈活地行動,是因爲多年來他一直在關注鄰居們的需要、聽他們講故事,了解誰能幫助什麼。(他是如此地樂於助人,以至於當他鄰居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時,他要求佟牧師在他入獄後收養他的兒子。)
「支持城市」之所以廣受歡迎是因爲它正好填補了一個需求。但佟牧師之所以能如此靈活地行動,是因爲多年來他一直在關注鄰居們的需要、聽他們講故事,了解誰能幫助什麼。(他是如此地樂於助人,以至於當他鄰居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時,他要求佟牧師在他入獄後收養他的兒子。)
過去的那份忠心是人們信任他現在還能堅持下去的原因。多年來,伯利恆浸信會一直爲移民開辦ESL(教外國人英語)事工,幫助沒有車的移民買菜,和提供社區聖經學習,並與當地鄰里協會合作清理垃圾、解決安全問題,以及舉辦節日活動。
「我們的方法論,至少在我的領導下,就是參與和服務,並通過建立關係來分享好消息。」 佟牧師說。他知道這一點做得並不完美,但「我們不能因爲做不對而什麼都不做。」
佟明璟現在的主要目標是「與我們附近的其他組織建立聯繫,」他說。這一點很重要——伯利恆浸信會並不是唯一在菲利普斯開展服事的團體。多年來,他們經常與其他教會或組織合作。佟牧師參加聯合會議、去參加社區領袖們的聚會,並與官員商討土地使用或住房開發的策略。
「我的整個生活都是爲了拓展福音,」佟牧師說。他鼓勵住在菲利普斯的教會成員將服事未信主的人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參與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並在這一路上成爲福音之光。「我們的整個生命就是一個活的祭物。」
硝煙瀰漫的大湖街還不足以把派博趕出這個社區。
有人砸壞了他的車,有人偷了他兒子的自行車。幾週前,一個男孩問他是否可以幫忙割他家草。派博說「可以」——當一個孩子想要工作賺點零花錢時,他總是這樣支持。但後來那個男孩帶著另一個朋友回來了,並試圖撬開窗戶。「諾爾和我坐在五英尺遠的地方,看著他們這樣做,」他說,「後來我打開門,他們逃跑了。」
 幾天後,派博聽到一聲撞擊聲,看到一輛汽車撞上了人行道。司機下車向一個人開槍並且打傷了他。「他的手流了很多血,」派博說,他接著撥打了911。
幾天後,派博聽到一聲撞擊聲,看到一輛汽車撞上了人行道。司機下車向一個人開槍並且打傷了他。「他的手流了很多血,」派博說,他接著撥打了911。
「這些年來,我最大的爭戰之一就是不要變得狹隘,」派博說。比起成功,他更能感受到失敗。「我最大的遺憾之一是我們在美國本地社區的影響似乎很小。」伯利恆浸信會也不像他希望的那樣多種族和多元化。社區犯罪仍然很常見——在最近這個季節更是如此。
不過,也有這樣的時刻:
「幾個禮拜前,我坐在後院的野餐桌旁吃午飯,」派博說,「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停下來說,『嘿,我很久沒有見到你了。你還住在這裡啊!我小時候經常在你的車道用彈弓打水桶。人們常告訴我說,我住的社區很糟糕,我會告訴他們——這不可能!牧師就住在街角。』」
派博總結說:要量化長期存在所帶來的各種影響是相當困難的。
同時,以福音爲中心的期望也很重要。
「當我讀到《彼得前書》時,」派博說,「彼得對被贏得基督的人的期望似乎並不包括去轉變文化。聖經期望是:繼續宣揚那召你之神的美善之處、繼續服事。有些人會被你感動以至於信靠基督,也有些人則會繼續惡言相向。」
派博接著說:「彼得說話不像一個城市重建專家。他使用了諸如『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彼前1:6)、『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彼前2:12)、『忍受冤屈的苦楚』(彼前2:19)、『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爲奇怪』(彼前4:12)等短語。」
換句話說,《聖經》並沒有應許,如果你搬進像菲利普斯這樣的社區,人們就會放下毒品和暴力、追求讚美詩的歌聲和穩定的家庭結構。
 「但他們可能會看到你的行爲,並將榮耀歸給神。」派博說,「你的工作就是在那裡,愛他們、宣講真理,解釋你所懷盼望的緣由。我的工作就是忠心,神的工作是多結果子。我們想看到果子,但果子不是我們留在城裡的理由。」
「但他們可能會看到你的行爲,並將榮耀歸給神。」派博說,「你的工作就是在那裡,愛他們、宣講真理,解釋你所懷盼望的緣由。我的工作就是忠心,神的工作是多結果子。我們想看到果子,但果子不是我們留在城裡的理由。」
他比以前少了很多擔心被人利用的感覺。「以前我自詡能看穿謊言,讓人在討錢的時候說話自相矛盾。」他說,「但漸漸地,主讓我明白,在審判日,精明沒有獎賞,愛才有獎賞。而耶穌的命令則是:要轉過臉去讓人打、要把你的衣服都給人、要走兩里路而不是隻走一里路,這些都讓我知道,被人利用是正常的。」
「耶穌關注的是殺死我的自私,多過關注誰得到了多少錢。我的問題應該是:我在基督裡面會不會得到滿足,所以被人利用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在這個社區附近工作了40年,如果重來一次,派博認爲自己還是會這樣選擇。「我真的相信,十年又十年地傳講神的全備真理,建立一個奉獻生命的教會,時不時地領受呼召爲耶穌做一些瘋狂的事,以這位偉大的神所教導的神學爲支撐,以及成爲這間城市中存在的榜樣,這些都會帶來很大的不同。」
於是他不斷僱傭孩子們修剪草坪,在附近慢跑時派發新約聖經,與無家可歸者交談。在弗洛伊德遇害後的幾週內,諾爾每天都去以非洲裔美國人爲主的大友誼宣教浸信會的食物分發處做志願者。而附近的其他基督徒則帶領社區俱樂部,種植社區花園,撿拾垃圾,在公園區做義工,和鄰居們一起禱告。
「如果當有人對我說,『如果你可以選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居住,那會是哪裡?』我會說,『諾爾在哪裡?』」派博說,「其次,我會問,『哪裡有需要?』」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iots in John Piper’s Neighbor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