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荷華大學研究生院第一年的下半學期,我選修了一門關於《白鯨》(Moby-Dick)這本小說的課。在那之前,我已經完成了本科學業,而且大學畢業後的幾年中有一段時間是爲雜誌寫美國小說評論。不過,我從未完整讀過這本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傑作——它通常被稱爲是美國最偉大的小說。我讀了很多關於《白鯨》的介紹和評論,這些評論給我的收穫就是知道了我其實從未讀過這本書。我的寫作經歷也讓我知道我應該讀這本書。現在,我需要更多的背景,我也需要有人督促我去讀這本書,我希望選修這門課程能夠迫使我在這方面下點苦功夫。
不過,比起這本著作本身,更吸引我的是教授這門課的老師。這門課由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教導,她是《管家》(Housekeeping)和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基列家書》(Gilead)的作者。羅賓遜的作品薰陶和指導過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從約翰·派博(John Piper)到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她的文字平實而抒情,思想堅韌而寬廣,立足於今生卻向永恆敞開。
她的作品優雅而奇特,常常摒棄章節的劃分和通常的情節進展方式,像禱告一樣蜿蜒地走向啓示。這些作品不像是小說,更像智慧文學;不像文學,而是思想本身。
羅賓遜在美國文學界算是一個相當「老頑固」的人物。還有哪位21世紀作家會像她在《基列家書》中所做的那樣,專注於描寫一個垂死的、對棒球、廢奴主義和喬治·赫伯特的詩情有獨鐘的牧師?還有哪個作家能把善良和美德寫得如此有趣?羅賓遜的這種寫作風格來自哪裡?我很想知道,《白鯨》對她意味著什麼?
我有一個這樣的猜測:《管家》的第一句話(「我叫露絲」)與《白鯨》的第一句話(「叫我以實馬利」)是一種呼應。我認爲,這兩本書都是通過一個高度反思性人物的離散思考看待現實,這個人物既是獨特的,又能代表人類的認知。這兩本書都運用了隱喻來探索存在的本質,並且對認知和語言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質疑。
可以說我在2013年秋天註冊這門課程時,我感到興奮,也有點緊張。但當我在寒冷的第二個學期第一天進入教室時,我的期待已經被一種懼怕所取代。寒假期間,我從華盛頓州調到愛荷華市開始的編輯工作在沒有任何提醒的情況下結束了。我妻子的自由寫作收入和我因教授本科寫作課程而獲得的津貼,對一個四口之家來說並不足夠,更不用說我們即將成爲一個五口之家了。
長期以來,「寫作決定出路」一直是我的口頭禪,但現在我已經很難在紙上寫出句子了。我已經開始懷疑當初離開華盛頓的決定(我在那裡從事了將近十年的新聞工作,我們計劃在完成我的文學碩士學位後再搬回到那裡)是否不明智?我是否錯誤地把對文學夢想的頑固追求當成了一個可敬的支點?
突然間,與羅賓遜一起讀《白鯨》的前景感覺像是一種奢侈,現在我沒有理由放縱自己去享受這種奢侈。當你都不知道該怎麼買菜的時候,怎能沉浸在偉大的名著中呢?更不用說寫作了。
這種焦慮,無論聽起來多麼合理,都顯示出更深層次的不信。在內心深處,我在質疑神的護理——「質疑」不如說是指責。我的基督信仰自從14歲時一個傳道人與我分享福音以來就一直存在,但卻充滿了臆想。是我讓環境蒙蔽了我對現實的看法。老話說的沒錯,鑽石的確需要好好擦拭。雖然有很多事情幫助了我,但卻是《白鯨》選修課幫助我設定了正確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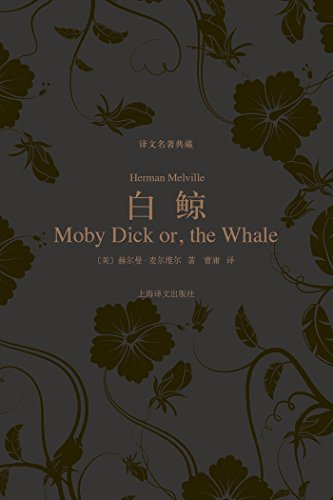 這門課在週三下午舉行,地點是弗蘭克·康羅伊閱覽室(Frank Conroy Reading Room),這是一座莊嚴的維多利亞式老建築,也是「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所在地。閱覽室裡一邊是高大的窗戶,俯瞰著冰封的愛荷華河;另一邊的玻璃書架上則陳列著校友們的作品,包括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華勒斯·史達格納(Wallace Stegner)、丹尼斯·約翰遜(Denis Johnson)、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李翊雲(Yiyun Li)等等。選修了這門課程的學生包括了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和翻譯家,他們來自本校的研究生寫作項目,還有客座教授和一些附近城鎮的旁聽生。當羅賓遜走上講台時,我幾乎聽到了所有人的凝重呼吸。
這門課在週三下午舉行,地點是弗蘭克·康羅伊閱覽室(Frank Conroy Reading Room),這是一座莊嚴的維多利亞式老建築,也是「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所在地。閱覽室裡一邊是高大的窗戶,俯瞰著冰封的愛荷華河;另一邊的玻璃書架上則陳列著校友們的作品,包括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華勒斯·史達格納(Wallace Stegner)、丹尼斯·約翰遜(Denis Johnson)、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李翊雲(Yiyun Li)等等。選修了這門課程的學生包括了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和翻譯家,他們來自本校的研究生寫作項目,還有客座教授和一些附近城鎮的旁聽生。當羅賓遜走上講台時,我幾乎聽到了所有人的凝重呼吸。
羅賓遜小說中的虛構人物有一種複雜的平民氣息。他們的深刻性,以及這思想固有的給人帶去驚訝的能力從未受到過質疑,但卻能夠以平實的語言轉達出來。他們的思想和嘴巴之間好像有一個隱含的分別,默認舌頭只是人類意識這一無底泉源的井口。在這方面,福克納(Faulkner)似乎有很多影響。
然而在課堂上,羅賓遜的智慧得到了充分展示。她說話總是用長長的、鼓舞人心的句子,這些句子的轉折和流向精煉且不可預測。她引用了丁道爾和當天《泰晤士報》的文章。她誦讀了約拿書的經文,引用了奧古斯丁、狄更生、海森堡、洛克,她對宇宙學、現象學、歷史和語言學也很有研究。作爲一名受過速記訓練的記者,我盡可能地在我兩歲女兒用橙色蠟筆塗抹過的黑色8.5 x 11英寸Moleskine本子上進行速記,希望以後能重新審視這些筆記。但另一方面,羅賓遜卻很少查閱自己的稿子。
我該如何描述她的聲音呢?可以說是淡淡的、沒有煩惱的。她沒有向聽眾推銷任何東西,配戴著一個領夾式麥克風,每次她的銀色頭髮落在上面時,麥克風的聲音就會受到影響。然後她會把頭髮撩上去,這時她的聲音會有一個變化,讓你覺得好像自己也在幫忙一樣。事實上,這是我對這門課的一個持久印象,一種講台帶來的引力,並透過講台進入羅賓遜思想的宇宙。
《白鯨》是一部出乎意料的小說,既吸引群眾,又離經叛道,既深刻又廣泛。它既是一本散文集,又是一本參考書,是聖經中的寓言,是莎士比亞式的獨白,是滾滾的海洋敘事,是一首散文詩。支撐這本書的是梅爾維爾筆下滔滔不絕的敘述者以實馬利——一位來自曼哈頓的流浪水手,他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個港口加入了「裴廓德號」("Pequod")成爲船員,這是一艘由狂熱分子亞哈船長駕駛的捕鯨船。
對亞哈來說,白鯨如同一個憤怒的、反覆無常的神。《約伯記》中對此也有令人難忘的描述。「你能用倒鉤槍扎滿它的皮,能用魚叉叉滿它的頭嗎?」上帝在該書的最後幾章中這樣論及利維坦(和合本譯作「鱷魚」——譯註),「你按手在它身上,想與它爭戰,就不再這樣行吧!」
亞哈對此的回答是:「哦,是嗎?願意打個賭嗎?」他已經被鯨魚吃掉了一條腿。
船長具有一種普羅米修斯式衝動,他拒絕接受人們通常用的那種嘗試性努力,這預示了這艘船的命運。然而,正如唯一的倖存者以實馬利敘述的那樣,裴廓德號的不守常規帶來了真正的超越,因爲船員們——包括黑人、美洲原住民、貴格會教徒和異教徒——在鯨鯊海獸出沒的大海上找到了一種團結一致的友愛。
在每一個主題上,羅賓遜都有發言權。她說,像惠特曼和林肯一樣,梅爾維爾培養了一種包容美學,與19世紀在歐洲扎根並在20世紀將其撕裂的民族主義思想不一致。是良知——而不是遺傳、母語或歷史——將個人聯合起來,並賦予他們在這個新世界的價值。她說:「《白鯨》站在歐洲哲學傳統之外的事實,不一定是一種對它的批評。」
羅賓遜這種對理解梅爾維爾的理解基於19世紀的新英格蘭宗教文化,她坦率地說,自從一位大學教授指派她寫了一篇關於清教徒的論文以來,她就一直對這種文化保持興趣。對此,她解釋說:「我確實喜歡閱讀前現代著作,那時的人對死亡有更多的認識。他們看到了太多的疾病、死亡和痛苦,才會對公平的問題感到困惑。對他們來說,這問題顯而易見,就像對《約伯記》的作者一樣,世界是由一個不同的、更神祕的法律所支配的。」
在課上,我們讀了來自愛德華茲和加爾文著作的摘錄,這兩位神學家關於人類尊嚴和墮落的觀點,以及神的旨意和人類責任之間的相互作用,支撐著梅爾維爾的形而上探索。她說:「恐怖和歡樂、甜蜜和可怕、苦難和榮耀……在基督教傳統中,這些東西是一起呈現的,而且並非彼此否定,也不是彼此競爭,而是有關係的,有樂趣的,在某種程度上成爲同一經歷的兩面。」
羅賓遜很喜歡《白鯨》。她的平裝本看起來像一個臃腫的抽屜,已經皺得無法修復了。每隔一頁都有標記。她讀過無數次這本小說,也反覆地把它當作過一種教導資源,但她仍然陶醉其中。她會長篇大段地朗誦其中的文字,有時會自嘲,有時徘徊在某些短語的轉折處,就像投入了一種私人的熱情。在朗誦了「獅身人頭怪物」一章中的這句話——「一片鏗鏘有聲似的寧靜,像一棵黃色的大忘憂樹,正在把它那無聲無息又不可數計的樹葉,越來越多地鋪開在海面上。」——之後,她嘆了口氣,說:「我們能說什麼?他有一種天賦。」這就是閱讀《白鯨》的方式:慢慢地,充滿期待地,帶著樂趣,帶著感恩。
羅賓遜說,像所有其他偉大的作家一樣,梅爾維爾關注的是知識問題。他的指導性問題是:「你如何從壓倒性的、不透明的事物中獲取對人類有意義的東西?」她聲稱,作者對捕鯨者、捕鯨傳說和捕鯨貿易中的體力勞動進行了乏味的、甚至是帶著強迫性的描寫,這與《聖經》中的現實主義概念有關,這種全面的世界觀堅持宇宙的不可捉摸性和每個人生命的意義同時成立。羅賓遜說:「在加爾文主義中,對你的最大要求是關注——關注神、關注他人、關注自己。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值得沉思的主題。」
這一說法打擊了我,但同時也給了我一個重新定位的思考。我一直在關注什麼?不是對神,而是對不如意的抱怨;不是對他人,而是對恐懼。我沒有在我的經歷中尋找智慧,沒有花時間在禱告中呼求。我懷疑有一種意識主動地在這個世界上做工,更不用說在我的生活中做工了。我一直在覬覦其他的經驗——更清晰、更少不舒服的經驗。
在一對一的訪談中,羅賓遜告訴我,她一直在閱讀威克里夫的信件,她被他所強調的爲自己所做不該做的事情悔改,以及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爲自己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悔改所感動。失敗和恐懼一樣,都有其用處。她說:「世界給我們的恐懼是我們發現自己的地方,因爲世界給我們的恐懼也是我們背叛自己的地方。」
在「噴泉」這一章中,本書對鯨類噴水孔做出了具體的描寫。以實馬利將海洋中央噴出的霧氣這一令人不安的景象變成了光照的隱喻。他說:「在我腦裡的種種迷雲疑團中,總不時地有直覺的神力顯現出來,以一種聖光來點破我的迷津。」
當我每週認真聆聽羅賓遜的講課時,我也在霧中瞥見了一束光。即便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被蠟筆塗抹過的課堂筆記,我也能感覺到古老真理正在破曉的快感。我並不是完全掌握了失去工作的意義,也不是說我有任何保證好像事情會按照我的計劃進行。而是羅賓遜爲我確認了,期待意義是多麼正確、多麼意義,以及期待對信仰生活是多麼重要。
教師所做的比教書更多,所教的比他們以爲的更多。羅賓遜對加爾文的評論讓我重新翻開《基督教要義》這一套兩卷的書。在我離開華盛頓之前,一位牧師朋友送給我的。羅賓遜對愛德華茲的思考讓我想起了我在大學二年級時讀過的講章,那時我第一次開始對上帝的榮耀、我的頑固和基督的贖罪之愛有了概念。這兩位神學家推動我回到聖經中,我在對現在的抱怨和對未來的擔憂中一直忽視了聖經。寫作的速度很慢,但現在寫作的渴望又回來了,寫作的熱情也會隨之而來。
在課堂的最後幾分鐘裡,羅賓遜讓大家提問。學生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她是如何看待霍桑的,梅爾維爾聲稱《白鯨》是爲他而寫。羅賓遜說:「我希望我能夠公平對待霍桑,但他的作品讓我感到毛骨悚然。」有一次,一個學生問羅賓遜是否相信有外星人。「我認爲我們肯定是唯一的人類,」她回答說,「但即使另有一個智慧生命,那也會是兩種『人』,這並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最後一次上課的時候,一個學生提出了一個我們都在想的問題:現在還有可能寫下像《白鯨》這樣的作品嗎?羅賓遜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寫一本就知道了。文學一次又一次地見證了這樣一個事實: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她從講台後面走了出來,繼續說:「我不是在談論自我欺騙。我說的是那種不需要文化認可的自信和自律。」
教師教的比他們以爲的更多。在接下來的幾個學期裡,我將與其他傑出的作家一起上課。我將找到慷慨的導師、嚴厲的讀者和鼓舞人心的同齡人。我還將參加羅賓遜的兩門課程,一門是舊約,一門是新約,但我記得在《白鯨》選修課之後的想法:如果我不得不在沒有完成所有課程的情況下離開愛荷華,那也不會是一種浪費。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找到了我需要的東西,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等待的東西其實是這個。那是一種責備,同時也是一種許可:關注、接受亮光、寫作。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ading Moby-Dick with Marilynne Robi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