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本文係「美國文化戰爭」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我們的社會在對待基督信仰上真的已經做出了決定性的轉變嗎?我們是否已經拋棄了一個對基督信仰基本持正面態度的文化世界,進入了一個對基督信仰持消極負面態度的文化世界?如果是這樣,我們是否應該讓承認這種文化轉變成爲我們看待自己——作爲堅定的基督徒——與周圍文化之間關係的正確視角?
亞倫·雷恩(Aaron Renn)在他爲《要事第一》(First Things)網站撰寫又廣爲流傳的文章中探討了這種從積極到消極的轉變,我在前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這一點,那是我關於新宗教右派崛起和美國文化戰爭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該系列的前兩篇文章分別介紹了美國文化戰爭的歷史和脈絡,以及將信念與文明禮貌切割的趨勢。
讓我複習一下。雷恩的分類法是這樣的:美國文化在1994年之前對基督教基本持積極正面態度,94年之後的20年裡對基督教基本持中立態度,但自2014年以來,美國文化對基督教轉爲消極否定的態度。我注意到,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和澳大利亞牧師斯蒂芬·麥卡爾平(Stephen McAlpine)都指出,文化轉變也是在那個時期發生的。
雷恩的分類法爲開啓這個話題做了很好的努力,因爲(1)很難否認過去10年的快速文化轉變,(2)雷恩的框架暗示了一種結論,即以前參與文化的方式現在已經過時了,也許適合以前的時代,但不再有意義了。
但雷恩的文章並沒有提供一個處方,如新的戰略或新的戰術;相反,它提供了對這一文化時刻的描述,從而促使福音派人士開闢一條新的路線。事實上,雷恩認爲有太多人仍然生活在過去,假設世界對他們來說仍然是積極的或中立的。他寫道:
福音派人士不應該將已有的戰略延伸到未來,而是可以而且應該認真地探討他們生活在一個對基督信仰消極負面的世界中意味著什麼。這個時代應該採用什麼策略?與以前的時代不同,我們需要各種方法來回應美國基督徒所處的各種情況。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可能需要試錯,以及一組具有不同技能和感覺的新領袖。
今天,我想指出這種思維方式的一些侷限性,因爲我相信我們所處的時刻比雷恩的構思和可能的建議更加複雜。在本系列下一篇文章中,我將談談我認爲這種方式最明顯的弱點是什麼。
首先,我們需要問,2014年是否是一個好的里程碑。生活在一個敵視基督教的世界中這種「感覺」是最近才有的嗎?
作爲一個在致力於宗教右派宗旨和目標的家庭中長大的人,我認爲我們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處於一個對基督信仰有敵意的世界了,這甚至是在雷恩聲稱我們從正面轉向中立之前。我在這個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卡曼(Carman)的歌創作於1992年——它記錄了美國滑向無神論的過程,並聲稱這個國家要度過這十年,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復興中回到神身邊。
如果我能回到過去,告訴青春期的自己,其實你仍然處在一個對你的信仰持積極態度的世界,但文化即將轉變爲對基督教持中立態度,我相信我會被以前的自己嘲笑,也會被我的家人嘲笑。像當時大多數福音派教徒一樣,我們確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對基督持負面態度的世界裡。而我又是在聖經地帶長大的!
這就是爲什麼我對雷恩提出的分類法保持懷疑——不是因爲它們沒有價值(它們幾乎總是有價值),而是因爲它們幾乎總是太整齊,而且它們通常與某種旨在動員選民集團的提案有關。政治參與成爲實現社會變革的最重要槓桿。(明確地說,雷恩的文章並沒有這樣做,但許多以他的工作爲依據的回應者卻這樣做了。)
也許逼迫的空氣是想像出來的,也許我們在90年代初擔心的那些可怕的情況被誇大了,雷恩是對的——我們當時是被愚弄了,以爲世界對我們是負面的,而實際上,我們只是對從積極到中立的變化做出反應。但是,在這樣一個可能是想像出來的文化中長大,這一氛圍對我們的文化參與方式以及我們如何看待教會履行其使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我13到14歲的時候,我寫了一系列短篇小說,講述2050年的基督徒因爲受逼迫而被趕出美國。)
更重要的是,後來我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與那些經歷過政治壓迫和真正信仰逼迫的人交流,才讓我看到了更廣泛的基督徒關注的問題,當我把注意力放在選舉獲勝上時,很多問題都被我出於方便忽略了或忽視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仍然同意青少年時期的自己所持有的原則和應對,但我對基督徒的關注範圍已經擴大,我對通過政治進行文化變革的期望也得到了修正。
因此,即便我認識到雷恩、凱勒和麥卡爾平指出的過去10年中文化情緒的轉變,我還是對採用「消極負面態度的世界」這一框架猶豫不決,因爲不管它有什麼優點,我已經很容易看到它如何縮小我們的關注範圍,扭曲我們對聖經的解讀。
「但是,」你可能會說,「那些試圖在政治上保持『超越』的文化參與派也對聖經有扭曲的解讀,對嗎?」沒錯,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點:我們都傾向於從我們試圖接觸的人那裡獲取線索。
雷恩的文章批評了與文化互動的那一派採取的策略,即從世俗精英的共識中「取材」。爲了吸引世俗精英或名人來到他們的教會,許多抵制老牌宗教右派的文化參與型牧師以「向右出拳,向左擁抱 」而聞名。換句話說,你想接觸世俗和精英,而你這樣做的方式是分享一種對其他階級或階層的蔑視感,他們不值得或不接受主流文化的青睞。
因爲感受到左派精英們的壓力,文化參與型領袖們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尋找「同步」他們觀點的方法,而種族和移民成爲兩個最明顯的接觸點。「他們在這些領域的言論越來越尖銳,越來越與世俗的政治立場相一致,」雷恩寫道:
同時,他們在熱點社會問題上的立場和言辭進一步軟化。他們經常談論全面支持生命,而較少談論子宮裡的孩子。在堅持關於性的傳統教義的同時,他們傾向於少談基督教的道德標準,多談教會應該如何成爲一個歡迎「性少數」的地方,強調教會過去在這方面的失敗。
我並不懷疑這種壓力的存在,而且一些文化參與型基督徒可能,甚至是無意地,在他們可以的時候與世界「同步」這些立場。年輕的文化戰士們在攻擊這一類的試探上是正確的。
話雖如此,好鬥的文化戰爭擁護者最終可能會做同樣的事情,但方向是相反的:向左打壓,向右擁抱。如果你試圖接觸到經常感到被遺忘的那部分人——他們聯合起來蔑視「左派」或「精英」——你會感到另一種壓力,要把你的關切與右翼播客和保守派脫口秀主持人同步。你關注的優先次序將首先轉向離你近的人群。在這種情況下,打擊種族不公正或回應《聖經》中關於關心客旅和寄居者的命令,很可能在你的道德責任列表上沒有那麼高的分數。文化鬥士們也不能避免在某些領域弱化聖經命令的誘惑,以避免觸犯社區內人們的敏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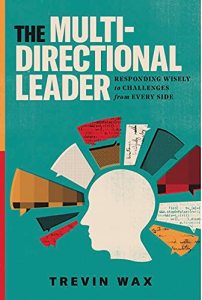 我在《多個面向的領袖》(The Multi-Directional Leader)一書中列舉了這種傾向的例子。西岸的一位牧師計劃在公開禱告的時候提到墮胎的罪惡,結果遭到了他手下的反對——他們擔心一些來訪者會受到冒犯。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人質疑他在以前的牧禱中所傳遞的基督徒對移民的關懷或我們國家的種族不公正問題上的立場。與此同時,南方聖經地帶的一位牧師卻經歷了相反的情況,教會成員期望牧師爲結束墮胎禱告,但當祈禱集中在槍擊受害者、移民或種族歧視受害者身上時,他們就會變得緊張。(「我們牧師是不是左派?」)
我在《多個面向的領袖》(The Multi-Directional Leader)一書中列舉了這種傾向的例子。西岸的一位牧師計劃在公開禱告的時候提到墮胎的罪惡,結果遭到了他手下的反對——他們擔心一些來訪者會受到冒犯。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人質疑他在以前的牧禱中所傳遞的基督徒對移民的關懷或我們國家的種族不公正問題上的立場。與此同時,南方聖經地帶的一位牧師卻經歷了相反的情況,教會成員期望牧師爲結束墮胎禱告,但當祈禱集中在槍擊受害者、移民或種族歧視受害者身上時,他們就會變得緊張。(「我們牧師是不是左派?」)
想像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世界對我們的姿態會影響我們的見證。不加批判地採用我們處於一個「對我們持有敵意的」世界這一觀點,會導致我們迴避不穩定的問題,通過縮小聖經的範圍來損害福音對文化所發出挑戰的廣度。如果認爲教會的使命只集中在「尋求巴比倫的平安」上,可能會導致我們對文化的塑造程度感到天真。但是,如果把教會的使命主要集中在反抗或重新獲得統治地位上,也會導致過於狹隘的聚焦和過於簡化的使命。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Didn't I Grow Up in the Negativ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