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試通過本文探討一個略微複雜、且可能頗有爭議的問題。我不把這個問題表述爲「信仰與政治的關係」或「政教關係」。因爲,當我如此陳述時,已然隱藏了某種「二元論」的前提,暗示「信仰」與「政治」或「教會」與「政府」首先是區隔、對立的兩個領域。
我把這個問題表述爲「福音的政治維度」。我希望表達的是:在福音的涵義中,原本就包含了政治的維度,並且能夠形成切實的實踐,而無須(無論有意無意)借助現代世界的政治概念(在某種意義上,也不構成與之「對抗」)。這個命題當然需要非常小心地解釋,因爲它可能引起許多誤解。
我需要先提出本文的首要意圖,是希望基於聖經、從一個可能被忽視的角度出發,對福音信息作一探討。並且我相信,這個探討對於基督徒在現代世界的信仰實踐是有意義的。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在新約中,耶穌和使徒們都對福音作了異常豐富的表達,從形式到內容(當然,福音的核心堅固不變)。那些福音表達有別於現代基督徒常常被教授或灌輸的「單張式信仰陳述」。在新約的福音表達中,我們能夠相當容易地辨識出許多主題和意象,不同的主題和意象從不同的角度向聖經的讀者展現福音,比如:「神拯救、贖回祂的子民」、「約的實現」、「獻祭的完成」、「神國度的降臨」、「回歸到神的園子」、「進入神的筵席」、「神栽種和收割莊稼」、「神帶領、牧養、尋回羊群」,等等。可是,我們比較少地明確指出,這作爲福音呈現的種種圖景,其中包含了清晰的政治因素。很多時候,即便當我們提及明顯的政治性詞彙(比方「神的國」)時,也會傾向於對其作一種「非政治」的解釋。
我們需要考慮,這樣的理解和「再呈現」,是否已經足夠努力地反映了聖經本身的表達?畢竟,在耶穌和使徒們的福音呈現中,充滿了「國」、「軍隊」、「王」、「審判」、「正義」這類元素。這些元素,難道首先不是政治性的嗎?甚至,「教會」這個詞,當它表示「人群的聚集」時,本來首先就是指政治性的集會,而非出於民族、經濟、教育這類原因形成的聚集。同樣,保羅也花費了許多筆墨,談論教會的治理。誠然,耶穌和使徒們也都強調了某種對「政治性理解」的矯正,比方「我的國不屬這世界」,但即使在這個表述中,仍然是以肯定的方式使用「國度」這樣的詞,只是指出它「不屬這世界」。
所以,我們是否錯過了一些什麼?保羅這樣說(以弗所書2:11-19):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爲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爲受割禮之人所起的。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爲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爲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爲一體,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因爲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保羅在這裡自然是作了一個精彩且清楚明白的福音表達:基督的福音使兩個老死不相往來的群體,外邦人與猶太人,合一了。在這個福音表達中,有若干重要的主題,比如諸約、獻祭、律法、和平。可是,還有一個主題也同樣很明顯,就是「國」。12節,保羅說外邦人原本的生存狀態,與神隔絕、沒有關係,「在以色列國民以外」。此處他的用詞是"πολιτεία"。這個詞在古代有強烈的政治意味,指城邦政制、公民身份,也可用於指稱更廣泛意義上的秩序。19節,保羅先是提到,因著福音,外邦人就不再是「外人」(ξένος)和「客旅」(πάροικος)。在古代語境中,這兩個詞,前者是指(有可能根據條約,或是傳統的待客習俗)長期居住在城邦中、享有很多福利但不具有公民權的外來者,後者則指完全的外來者、陌生人,兩者與國民在政治地位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差異。保羅繼續說,現在他們成了「同國裡的人」(συμπολίτης)。這個詞的意思是「公民同胞」,即同一城邦的公民。
所以,保羅在這個段落中,接連運用了幾個字詞,都帶有相當強烈的政治涵義。借助這些詞彙,保羅描繪的圖景是:在某種意義上,福音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適合使用政治詞彙來描述的關係和結構。現代讀者可能有一種直覺,把這裡的表達認作「比喻」。但是,有一個微妙的問題是:保羅這樣說的時候,教會還不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現象,或者說,當時的讀者並不像現代讀者那樣有一個清晰的意識,認爲「教會」是與政治團體截然不同的機構/組織。所以,大約現代人更能接受這是一個「比喻」,而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這裡幾乎找不到「喻體」。古代的讀者(尤其是希臘人,而保羅這番話又正是在對希臘人講的)不太可能錯過這個福音表達中明顯的政治意味。
另一個至爲明顯的例子,就是新約中「教會」(ἐκκλησία)一詞的運用。這個詞本身就是指城邦的公民大會,一個享有最高權力的政治集會。對當時的希臘人而言,這個詞的政治意味非常強,而新約恰恰用這個詞來指稱教會。
福音書中,只有馬太福音16章和18章,耶穌兩次提到「教會」,兩次都談論教會的權柄,後一次甚至是很具體的懲戒程序。使徒行傳第一次提到「教會」,則是在第五章,剛剛發生亞拿尼亞夫婦不服從使徒、遭罰而死,「全教會都懼怕」。
因此,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思考:如果新約希望對福音作一種「與政治無關」的表達,爲何如此直接而不加解釋地運用政治詞彙?至少,我們有理由說,政治圖景是新約用來描繪、呈現福音的眾多圖景中的一幅,而且,看起來它絕非比較不重要的那一個。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有必要考察聖經,並對自己慣常的預設加以反思。自文藝復興以降,一個顯著的過程是所謂「政治」的領域逐漸獨立,形成了一套自主的規則、話語、價值、論證。這正是需要反思的:聖經如何界定政治?
馬太福音12:22-32: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啞又瞎的人,帶到耶穌那裡,耶穌就醫治他,甚至那啞巴又能說話,又能看見。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啊!」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爲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我若靠著 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傢俱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這是特別有趣的一個段落。通常,基督徒們的注意力都被難解的「褻瀆聖靈」問題抓住,進而注意整段談到「趕鬼」這類屬靈的事件,反而錯過了耶穌在這個段落中表達的強烈的政治涵義。
這個段落始於耶穌的一次趕鬼行動,眾人並不很有意識地宣佈祂是「大衛的子孫」,以色列王權的擁有者。作爲敵對方出現的法利賽人表示,耶穌的權力來自於「鬼王」(ἄρχοντι τῶν δαιμονίων)。耶穌對此的回應,談到「國」(βασιλεία,王國)、「城」(πόλις,城邦)和「家」(οἰκία,家庭),這三個詞也就是古代人對政治秩序發生路徑的認識,從家到城邦,再到城邦聯盟或王國。耶穌指出在這三類政治體中,有一種情況將完全地破壞秩序,就是「自相紛爭」,分裂,亦即內亂。這一點同樣是古代人的政治共識。28節,耶穌說,如今在各位眼前發生的,是一種秩序的根本性轉變,神國(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θεοῦ)的秩序當然不可能有內亂,因爲帶來新秩序的聖靈不可能與神不合,也就取消了內亂的根源。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在31節耶穌說「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恐怕也有一層含義是,對帶來合一的聖靈的攻擊就等於否定或矮化神國的總體秩序,不承認神國、神的統治,不接受人進入神國的方式由神規定,自然是「不能得救」的大罪。
不過,令人感興趣的是常被忽視的30節。耶穌說「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這句話緊鄰著「褻瀆聖靈」,或許也是被忽視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句話正說明了神國秩序(政治)的原則。當神國來到的時候,將會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現象:「收聚」(συνάγω)與「分散」(σκορπίζω)。一個人群將被聚集起來,在此之外的,就都分散。而決定或帶來這一聚集的,也決定了這兩種狀態區分的,是耶穌自己。凡是與耶穌相合,就聚集起來,並且參與他的收聚行動;凡是不與耶穌相合的,就分散。耶穌使用了許多明顯的政治詞彙,來描述和呈現神國秩序的建立,也就是一種因他而有的、人群的「聚集」和「分散」狀態。福音在此世的效果,也就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福音的政治表達,也就是因基督而有的人群聚集與區隔。
進一步,基督如何實現他對人群的「聚集」和「分散」呢?在這個段落的上文,給了答案,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馬太福音12:17-21說道:
「看哪,我的僕人,
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裡所喜悅的,
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他不爭競,不喧嚷,
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耶穌建立神國秩序的方式,是祂的降卑、憐憫和公義。聖子進入世界,成爲人的樣式,存心謙卑,以至於死在十字架上,爲罪人代贖完全,第三日復活,叫那些不靠行爲、只靠信心的人,得以領受祂白白的恩典。於是,人群分開,教會建立,神國在這世上被人看見,顯出神的榮耀來。將來基督還要來施行審判,將神國完全顯現出來。
聖經確實向我們描繪了一種政治圖景,但它對神國秩序的定義,乃是以道成肉身、爲人犧牲的聖子耶穌爲中心。神國政治圖景的展開(人群的聚集與分散),同樣是以降卑受苦的基督爲中心,進入神國的人,也將效法耶穌受苦的樣式。在這一點上,神國的政治就與這世界的政治截然不同。
不過,若我們觀察今日的世界,卻又會發現存在一種極大的艱難。
如前所述,聖經使我們看見,對於福音,能夠作一種帶有強烈政治意涵的表述和呈現,即神國秩序因基督來到、聖靈的工作而牢固地建立起來,人群被分開。這就是政治。可是,我們需要思考,爲何今日我們談論福音/信仰/教會與「政治」的聯繫會產生相當的顧慮?既然聖經向我們呈現了一幅政治圖景,那麼,它在此世的生活中爲何模糊不清?
事實上,聖經亦向我們指明了福音政治圖景遭遇的危險。啓示錄13章描繪了魔鬼在世間的行動:大紅龍站在海邊,從海中上來一個獸;獸有七頭,其中一個頭「似乎受了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跟從獸,又敬拜龍與獸;又有另一個獸從地中上來,能夠行前一個獸的權柄,它給人受了一個「印記」。
儘管這個段落充滿了奇異的圖像和符號,但有一個基本的框架值得注意,就是魔鬼不斷地模仿、裝扮三一神的存有和行動。龍扮作聖父,第一個獸扮作聖子基督,第二個獸扮作聖靈。它們模仿了基督的死和復活,模仿了聖靈降下與改變人心,模仿了招聚人來敬拜。有許多人會被迷惑,去崇拜魔鬼。他們之所以被迷惑,是因爲魔鬼相當成功地僞裝成了三一神。
這樣,我們可以略微反思,爲何聖經呈現的以基督爲中心的「神國政治秩序」,今日很少有人談論。一個相對簡單的回答就是:魔鬼在此世的活動模仿了神國的政治秩序,令人對此產生了很大的迷惑。
按照極簡的歷史敘述,教會建立之初,事實上就表現爲一個具有清晰外部邊界和內部治理結構、形成特定秩序的共同體。羅馬帝國對教會的逼迫,很大程度上是因爲羅馬這個已經很成熟的此世政治體遭遇了一個帶來強烈陌生感的群體,羅馬人意識到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秩序,迄今爲止能夠包容(或壓制)一切民族、風俗、宗教的帝國無法包容它。於是,就必須消滅它。
而當君士坦丁聲稱歸主,就啓動了一個新的進程,一方面看來似乎帝國比原先的立場大大後退,不再逼迫教會,甚至使基督教成爲官方宗教;另一方面則開始了兩種秩序的溝通進程,在某種程度上,帝國通過模仿教會而消除了起初遭遇的那種不可磨滅、無法迴避的陌生感。二者之間的這種溝通到中世紀逐漸進展爲國家-教會的二元結構,進一步又在雙方之間造成了許多觀念的融合、借鑑、交換、平移。到中世紀晚期,我們可以看見,與教會世俗化進程同步發生的,恰恰也就是國家的神聖化。由此,更進一步,在一種與教會和神學有著深刻糾纏的國家形態之基礎上,現代世界逐漸成型。
現代國家形態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體,事實上,它在許多方面、在相當的深度上「模仿」了基督教會,比如:某種「建國神話」(尤其以「出埃及」式的解放敘事爲代表),被奉爲神聖的經典文本(可能是革命宣言或一部憲法),先知/君王式的開國元勳(呈現爲紀念碑、石像甚或「不朽」的肉身),不斷「生產真理」的機制(學者扮演祭司的角色),要求成員效忠(宣誓),對「敵人」的識別與嚴厲鬥爭,大眾參與的特別節日和儀式,等等。
如果我們同意前面所述,福音的政治性體現於一種以基督爲中心(標準和動力)的人群「聚集」和「分散」,具體形式就是教會。那麼,現代國家則是以另一些東西爲中心(很不同的標準和動力),構成人群的「聚集」和「分散」,具體形式就是民族國家。在現代國家中,可能首先以民族認同或者政治意識形態形成共同體,而其背後隱藏的那些不同的動力,正好反過來定義了現代的「政治」,也由此確立了政治與信仰領域的區隔。這類動力,可能被解釋爲人對利益或榮耀的追逐,可能是恐懼的激情,可能是經濟的需要,可能是群居的本能,等等。對於這類因素的探討,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知識和文獻,就劃定了一個與宗教無關的政治領域。
如果我們同意,聖經提示了魔鬼善於模仿神,那麼,就有必要反思基督的教會在現代世界面臨的一個危險:就是教會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現代國家對政治的種種定義和操作,由於這類定義和操作表面上與基督教信仰頗有相似之處,若教會欣然接受之,就可能引起更多的問題。比方,現代國家建立在識別絕對敵人的基礎上,識別的標準一定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而教會遭遇這類觀念時,由於「與敵人爭戰」、「人群要分開」的心態乍看起來與聖經教導有相似相通之處,就有可能接受,卻對背後的標準和動力反思不足。
最大的危險在於:教會可能偏離基督的福音,把另一些東西(甚至可能是「福音的果子」)當作人群「聚集」和「分散」的標準及動力,「愛的感覺」、社會公平、某個政黨的政治綱領、物質的繁榮、恰當的教育,都可能進入這個清單。與之相對應,教會在現代世界卻日益失去了以明白無疑和正式的方式確定、處理真正異端的能力。因此,情況可能變成:一方面,異端層出不窮、得不到有效處置,另一方面,持有正統信仰的基督徒之間,卻常以對待異端的方式彼此爲敵。教會在現代世界無力展現出起初那種令世人感到陌生的、福音的政治維度;教會至多只是踏進世界的政治領域、以世界熟悉的政治和文化定義開展某些行動(哪怕行動本身表現得很「激烈」,或者「很有成果」)。
如果我們正在考慮如何「應付」這世界的政治形勢,那麼,就有必要再次回想宗教改革。因爲,真正令宗教改革形成不可阻擋之勢的,並非對羅馬教會腐敗及教會介入世俗政治的批評,而是關於重要神學議題的思索、分辨與論證。
改教家們最爲關心,甚至不惜鬧到彼此分開的議題,第一,世人究竟如何得救,如何判斷是否得救;第二,是聖禮究竟有幾個,具體要怎樣施行。如果從「福音的政治維度」出發觀察改教家們的關注點,不難看到,這兩方面的神學議題,在實踐中一定會很快指向對教會共同體的辨識與規管——人群因何聚集、如何聚集、又如何分開。換句話說,宗教改革宣稱乃是恢復真正的基督教、回到本源,從這個角度觀察,也就是恢復了聖經所講論、規定的「聚集」與「分散」,亦即恢復了福音正確的政治維度。相較之下,當時羅馬教會的錯誤,雖然表現在販賣贖罪券、教廷專權、教士腐敗之類的現象,但更深的錯誤,一定在於對福音的認識和表達。在這一點上,當羅馬教會日益追逐此世的權力和榮耀,也就離降卑犧牲的耶穌基督日益遙遠,離基督這個福音政治維度的內在根基日益遙遠。
隨著宗教改革運動進一步展開,對救恩論與聖禮的關心,進一步體現於聖經論。因著追求更清晰、更符合神命令的救恩論與聖禮,必然不斷推動對聖經作爲權威的敬虔心態,與研究、翻譯、教導聖經的熱情。而聖經的翻譯和研究則繼續反過來推動教會的改革。
不過,罪人總是容易遺忘。隨著時間的流逝,基督徒們的注意力似乎越來越從改教家們起初關心的救恩、聖禮、教會和聖經的限定,轉向這世界發生的事。這或許是現時代基督徒們面臨的更大問題。如果「如何進入世界」成爲常常要考慮的事,那麼,大有可能,基督徒們會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極大的不確定性。因爲這世界的現象、潮流、「風」本就是變動不居的。基督徒們雖然絞盡腦汁、終日辛勞,最大的感受卻可能是常常詢問:「又有新變化了,我們要怎樣調整呢?」、「牧師你懂人工智能和區塊鏈嗎?」這世界的政治形勢、政治「信條」、政治文化在不斷改變,基督徒們能夠做什麼呢?抓到了某個現象,或借鑑、或反對,然後又會有新的現象出現,期待著另一種不同的反應。教會以如此方式日益進入世界,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堅定根基,因爲這樣的進入方式本身就意味著隨著現象不斷改變。這恰恰不是宗教改革對「改革」的定義。
當然,時代在變化,環境不同了。可是,我們仍然應當像當年的改教家那樣,渴慕並竭盡全力「回到」聖經的本源。若論到政治,今日我們仍然應當竭盡全力恢復聖經所展現的福音的政治之維。今日,我們應當如何正確地聚集與分開?能夠對這個世界紛繁複雜、快速變動的(政治)現象作出回應的,依舊是古舊的福音。改教家極度重視的聖經與聖禮,仍然是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出發點。
今日,高舉聖經,意味著釋經講道;嚴肅對待聖禮,意味著教會建制。聖經和聖禮是基本的信條;釋經講道和教會建制是在處境中謹慎的應用。
講道者應當懷著聖經所說的忌邪之心,萬分嚴謹地對待經文,運用適當的方法將文本解開,並接受由此而來的教導。講道者嚴謹地釋經,同時又是在建造教會,以聖言招聚神的子民——「聚集」起來,聽神的話,且要順服,然後,「天天彼此相勸」。一個以聖道爲中心的基督徒群體,必然接受由神的話管理自己,而非操縱神的話以實現其目的。
至於聖禮,洗禮有一重要涵義,即確認並宣告一個人爲基督的門徒,接納他加入基督的身體。而聖餐,則有一方面的含義,就是確認這個人與基督聯合,繼續地保持在基督的身體中。從這些意義觀察,聖禮事實上構成並維護了神子民群體的邊界。一間以敬畏之心施行聖禮的教會,必然詢問「聖禮的意義爲何」、「誰能施行聖禮」、「誰能領受聖禮」這些問題。教會的建制並非出於管理的方便,而是福音政治維度的必然結果。
聖道與聖禮的正確施行,又與聖靈的工作不能分開。真信徒必然有聖靈內住;沒有真信心的人,必然沒有聖靈。有聖靈內住者,必然聽見了神的道就順服,也必然領受聖禮的諸般好處;反之,則必然表現出對聖道的敵視,也必須被排除在聖禮之外。聖靈的工作絕不與聖道和聖禮相悖,並由此區分神的子民群體;聖靈的工作則顯明和招聚以及驅除那些不屬於這個群體的人。所有這些綜合起來,仍然回到福音的政治維度,回到福音使人群發生的聚集與分開。
最後,我們還必須意識到,正確地施行聖道與聖禮,也就是不斷傳講和見證那位降卑、受苦和犧牲的基督。正是基督自己,使得人群所發生的如此聚集與分開,與世界中發生的聚集與分開完全不同。
教會不需要因爲自己在這世界的政治活動中顯得格格不入而感到抱歉。嚴格說來,教會不需要做些什麼,向世人證明福音除了基督並祂釘十字架,還要加上任何東西、任何行爲或信念。教會不需要被人的設想、願望和情感牽引著進入世界、改變這世界的政治,教會只是單純地以其存在本身,迫使世人觀看、遭遇一種陌生、卻是純良與美好的秩序,迫使世人觀看聖經所說的罪如何得到處理,迫使世人觀看永生神的榮耀如何在一群罪人身上顯露出來。也唯有如此,教會才能有意識地分辨和擊敗撒但對神和神國秩序的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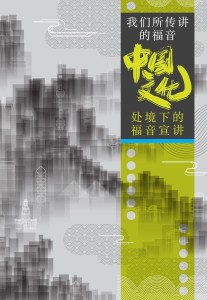 今日世界的政治,變化極快且多端。人群分分合合,人們找到敵人並與之戰鬥,然後發現如此敵對的背後,竟隱藏著深深的虛無,進而不得不以持續不斷地敵我區分來掩蓋這虛無,似乎如此還能賦予自己一點生氣。人必須用敵人來作自我定義,因爲自己的腳下沒有根基可以依靠。
今日世界的政治,變化極快且多端。人群分分合合,人們找到敵人並與之戰鬥,然後發現如此敵對的背後,竟隱藏著深深的虛無,進而不得不以持續不斷地敵我區分來掩蓋這虛無,似乎如此還能賦予自己一點生氣。人必須用敵人來作自我定義,因爲自己的腳下沒有根基可以依靠。
一方面,教會不能脫離這世界,不能拒絕談論政治;另一方面,教會亦不能將自身的任務辨識爲簡單地進入世界、贊同或反對某種政治。教會好像一個天國的空間,在這世界打開,它在這世界,又不屬於這世界。在這裡,人群以世人無法想像、不能理解的方式聚集和分開,其目的都是爲了傳揚和敬拜那位降卑受苦、死於十架的基督。
撒但或許可以模仿基督的死與復活,卻絕不能模仿十字架,因爲撒但至終乃是意圖竊取神的榮耀,他不能理解聖子放棄榮耀、爲罪人走上十字架的恩典。
我們確實處在一個複雜、令人沮喪的環境中,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單單需要基督的福音。基督呼召一個人,乃是呼召他來效法自己,呼召他背起十字架,呼召他來受死。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並非只是「不從國教」,在其深處的,乃是自願受苦、甘心背十字架的心志。在我們之前的許多聖徒,或許沒有很好的神學,但他們出色地向世人表達了福音的陌生感。今日,對我們這些基督徒而言,或許特別需要考慮在有清晰神學的基礎上作出同樣的表達。
編注:本文摘自《我們所傳講的福音:中國文化處境下的福音宣講》,該書由吉隆坡歸正福音資源中心於2020年出版,您可以在這裡下載本文的中文 | 英文P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