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什麼都很順利。
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在經歷了60年代末充斥全國的暗殺、抗議、性和毒品之後,帶來了全美的屬靈復興。
1976年10月,《今日基督教》報導說:「福音派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北美宗教界的老大。」蓋洛普調查集團和《新聞週刊》都把這一年稱爲「福音派之年」("The Year of the Evangelical")。人們對這個詞是如此陌生,以至於大衛·威爾斯和約翰·伍德布里奇還共同編寫了一本名爲《福音派:他們相信什麼、他們是誰和他們有什麼改變?》(The Evangelicals: What They Believe, Who They Are, Where They Are Changing)的書。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1981年初,在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和全國宗教媒體網絡(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的一次會議上,「一位又一位講員把80年代稱爲『福音派的十年』,這是保守派的繁榮時期,尤其是對那些關注回歸傳統道德的人而言。」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1981年初,在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和全國宗教媒體網絡(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的一次會議上,「一位又一位講員把80年代稱爲『福音派的十年』,這是保守派的繁榮時期,尤其是對那些關注回歸傳統道德的人而言。」
但在接下去的十年裡,福音派內部的區別開始產生和分化。巨型教會的數量猛增,每個教會都有名望比生命還大的領袖。金·貝克和塔米·貝克(Jim and Tammy Faye Bakker)夫妻倆和吉米·斯瓦格特(Jimmy Swaggart)之類的電視佈道家開始走紅,又很快因爲醜聞而黯然退場。道德多數派(The Moral Majority)幫助羅納德·里根當選,然後又不得不解散。
1990年,「我接到了樂馬可(Mark Noll)的電話,」時任戈登-康威爾神學院教授的威爾斯說。樂馬可告訴他,皮尤研究中心正暗示要給樂馬可(當時是惠頓學院的歷史和神學教授)、威爾斯和加爾文神學院教授科尼利厄斯·普蘭丁格一筆研究資金,讓他們寫寫福音派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當時大笑,」威爾斯說。這種研究經費不容易落地,他也不知道皮尤爲什麼會給他錢做這事。
威爾斯飛快地用幾句話答覆了樂馬可。他以前從來沒有研究過這個話題,甚至沒有做過很多思考。但從他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情況來看,他的想法——現代教會正在丟棄福音的中心地位——似乎是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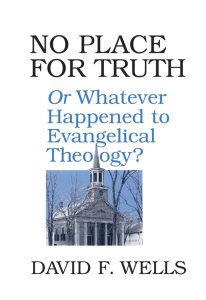 皮尤研究中心的確後來給了這筆研究經費,這是個很好的投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樂馬可寫了《福音派心智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普蘭汀格寫下了《本不該如此》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而威爾斯則完成了《真理無處容身:福音派神學出了什麼問題?》( No Place for Tru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皮尤研究中心的確後來給了這筆研究經費,這是個很好的投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樂馬可寫了《福音派心智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普蘭汀格寫下了《本不該如此》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而威爾斯則完成了《真理無處容身:福音派神學出了什麼問題?》( No Place for Tru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真理無處容身》的市場反應很好,一些有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都接受了這本書,他們認爲威爾斯是對的。他們的反應是開始了一個會議,然後發表了《劍橋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接著成立了「認信福音派聯盟」,以促進以福音爲中心的教會帶領。
「在我的圈子裡,(威爾斯)已經非常有名,人人都在說他的著作。」基督聖約教會主任牧師凱文·德揚這樣告訴福音聯盟,「無論你知不知道,『共同致力福音』(T4G)和『福音聯盟』(TGC)受到了他作品的影響。福音派教會,尤其是改革宗傳統的教會,都把他的話銘記在心。我們要重新找回神在教會和神學中的分量。」
 威爾斯並不是在福音派社區裡長大的,甚至都不是在美國社區裡長大的,他出生在津巴布韋(當時叫羅得西亞)。
威爾斯並不是在福音派社區裡長大的,甚至都不是在美國社區裡長大的,他出生在津巴布韋(當時叫羅得西亞)。
他的父母並不是宣教士,事實上,他們還反對威爾斯信主。當他在葛培理爲期一週的佈道會中擔任志願者時,他的媽媽一直把他鎖在屋外不讓他進家門。
他之所以出生在非洲是因爲很多很多年前,住在威爾斯的蘇格蘭外婆與丈夫離婚,獨自坐船前往南非,坐著牛車來到了羅得西亞。「她是一個強悍的人,」威爾斯說。(多年以後,學生們也用這個詞描述他)。
外婆嫁給了一個羅得西亞人,並生下了一個智力超群的女兒,但卻禁止女兒上大學。於是,威爾斯的母親找了一份祕書的工作,不知怎麼就遇到了威爾斯的父親,他的家很偏僻,門口的路只有土路。他的膽子也很大,16歲時就謊報年齡加入了英國騎兵部隊,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一次成功仗劍衝鋒,然後成爲羅得西亞的地區專員和法官。
威爾斯家中從小就沒有電,也沒有室內廁所。但他有母親的頭腦、父親的膽識,以及寄宿學校的教育。在南非開普敦大學讀書時,他曾沉迷於激進的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我的孩子們一直不相信我說的話,但這絕對是真的。」他說。
有一天,他看到一些海報,這些廣告呼籲大家去聽一個英國基督教演說家的講座。一對基督徒朋友邀請他去,他也去了,但他沒有留下來聽完。
 「講員是約翰·斯托得,」威爾斯回憶說。「我確實在他講的時候就溜了,我覺得他講的太激進了。」
「講員是約翰·斯托得,」威爾斯回憶說。「我確實在他講的時候就溜了,我覺得他講的太激進了。」
但兩週後,當他和其他建築系學生在山上畫畫時,他聽到教授談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斯托得所說的這一切都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他後來這樣告訴國會山浸信會的牧師狄馬可。
威爾斯對耶穌的熱忱超過了對馬克思的熱忱,他立刻想去做牧師。他的朋友們告誡他要放慢腳步,於是他完成了建築學學位,知道在津巴布韋沒有就業機會,便前往英國。他在1962年抵達英國時,沒有工作,沒有住處,也沒有父母的支持。
「我在倫敦遊逛,最後我來到了約翰·斯托得的教堂,我敲了敲門。」威爾斯說,「他把我帶進他的辦公室,我們進行了一次談話。過了一會兒,他說:『你住在哪裡?』我說:『好吧,我其實沒有地方住,』他說:『來和我一起住吧。』」
威爾斯於是住在斯托得的教堂裡,一邊當建築師,一邊思考如何成爲牧師。他每天都在聽著他的室友們——六到八位諸靈堂的單身牧師——討論教會問題,週末則在諸靈堂聽斯托得講課,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聽鐘馬田講課。
 有一次,威爾斯的一位舍友提醒他如果讀神學的話有可能獲得獎學金,而威爾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獲得獎學金。「我是個移民,在英國國內呆的時間又不長,」他說,「但我確實後來申請了一個神學院,當我拿到一個包括生活費和學費在內的獎學金時,我傻眼了。」
有一次,威爾斯的一位舍友提醒他如果讀神學的話有可能獲得獎學金,而威爾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獲得獎學金。「我是個移民,在英國國內呆的時間又不長,」他說,「但我確實後來申請了一個神學院,當我拿到一個包括生活費和學費在內的獎學金時,我傻眼了。」
威爾斯於是在六年內完成了三個學位:倫敦大學的神學學士(BD),三一福音神學院(TEDS)的神學碩士(ThM),以及曼徹斯特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來他還在耶魯大學做了一些博士後研究。
他的浪漫生活也同樣進行的很緊張。當他和薛華(Francis Schaeffer)一起在避難所團契(L'Abri)服事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簡(Jane)的女孩,並有了 「相當迅速的浪漫」——他們在10天內訂了婚。(「那段時間很特別,」他笑著解釋道。「接下來的一週,簡要去希臘,然後回美國,我則要回倫敦。我們必須相當快地確定我們的關係。」)
一直以來,他都在聽斯托得和鐘馬田的講道,和朋友兼同學葛尼斯激烈辯論,並且觀察舍友們如何在生活中實踐神學。1969年,他和簡移居美國,在三一福音神學院教神學,1979年他接受了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邀請前往該校任教直至退休。
威爾斯以前的學生們用 「很樂意聽他講」、「給教會的恩賜」、「如果你需要一個人摟著你,就不要找他」這樣的話來形容他。
「他以作風強悍聞名,但他又是個好老師,他這兩個特質都具備。」德揚說,他在大學裡讀了威爾斯的著作後去了戈登-康威爾神學院。「我盡可能多地修他的課。」
「他是我聽過的最棒的教授,」狄馬可說。「他的講課超級棒——精準,而且出色。他非常擅長給出參考書目,鼓勵學生們去了解別人在寫什麼。我是他的忠實粉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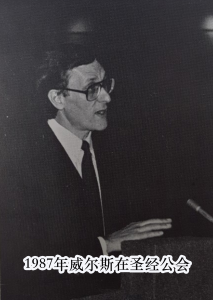 到1990年,威爾斯看到的福音派團體墮落讓他感到擔憂。
到1990年,威爾斯看到的福音派團體墮落讓他感到擔憂。
「當我第一次來到美國時,在廣泛的福音派世界中有一個非正式的教義共識,」他告訴福音聯盟,「這個共識雖然沒有涵蓋每一個神學主題,但它確實涵蓋了重要的主題。當我回顧歷史時,這一切似乎相當清楚,二戰後不久,福音派這個偉大的信仰聯盟始於美國的葛培理、哈羅德·奧肯加(Harold John Ockenga)和卡爾·亨利(Carl Henry),在英國則始於斯托得和鐘馬田,如果可以的話我還可以算上薛華。」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小。「但我不認爲這種變化純粹是因爲這些人的個性問題,」他說。「背後發生的是他們所代表的世界——一種更有教義結構的世界——正在瓦解。」
威爾斯能看到人們的注意力時間在縮短(《娛樂至死》一書出版於1985年),教育在退步(作爲回應,古典學校在80年代初開始重新興起),道德在消退。
因此,當樂馬可要求威爾斯給皮尤研究中心寄一些文字好申請資金時,威爾斯寫下了幾句話,說文化如何包圍和扭曲教會,現代社會如何使教會的思想和對神學真理的胃口變得遲鈍。
六週後,皮尤批准了研究資金的撥款提案。它很慷慨,允許三人在兩年內全職進行研究和寫作。
「大約有20分鐘,我只是在爲此歡呼雀躍,」威爾斯說。「然後我想,哦,不,我做了什麼?我沒有資格寫這個。我真的沒有。」
 威爾斯把自己關在戈登學院圖書館一間小小的、沒有窗戶的自習室裡。他花了一年的時間閱讀,從葛尼斯關於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600頁論文開始,然後幾乎讀完了伯格的所有作品。 他還讀了馬克斯·韋伯等社會學家的著作,也讀了關於美國歷史和對廣告現象的研究。幾個月後,他仍然不知道該寫什麼。
威爾斯把自己關在戈登學院圖書館一間小小的、沒有窗戶的自習室裡。他花了一年的時間閱讀,從葛尼斯關於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600頁論文開始,然後幾乎讀完了伯格的所有作品。 他還讀了馬克斯·韋伯等社會學家的著作,也讀了關於美國歷史和對廣告現象的研究。幾個月後,他仍然不知道該寫什麼。
「我仍然沒有得到足夠清晰的畫面,」他說。「我會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得到幫助,但我無法看到整個畫面。」他試圖在著作中解釋基督和文化之間的關係,隨著人口從農場轉移到城市,資本主義和技術加快了日常生活的節奏,每個人不同的世界觀,在狹小的空間裡擦肩而過,產生了更多的相對主義。
「催生了我們現在這種社會的是現代化。」威爾斯說,「由此產生的公共環境就是現代性(modernity)。但這些詞——現代化和現代性——對很多人來說都很抽象,我怎樣才能用一種他們能夠理解的方式向我的讀者解釋發生了什麼?」
他在馬薩諸塞州一個名叫溫罕(Wenham)的小鎮找到了答案。戈登學院放假之後,這個小鎮人口只有4875人。威爾斯在《真理無處容身》的開篇解釋了清教徒是如何在1635年的一次佈道會後在溫罕定居下來,並分幾個階段進入了現代化:電報讓位於廣播、電視和互聯網,農田讓位於郊區大宅子,馬匹被火車、汽車和飛機取代。
在這些階段中的某個時期,溫罕和其他其他美國小鎮一起跨過了一條鴻溝,威爾斯在《真理無處容身》中寫道。「彷彿製造更好的汽車、更好的飛機、更好的藥品和更好理論的能力,也就意味著製造更好自我的能力——不僅超越我們自己的死亡,這將是一個不小的壯舉,而超越我們自己的敗壞,這將是一個更大的壯舉。」
「所以很多人不再相信共通的人性,他們不再相信所有的人類有什麼共同之處,」他告訴福音聯盟。相反,「他們相信自我——每個人最裡面最核心的東西,這對他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不同於其他任何『自我』。這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極端相對主義的根源:人們不僅有自己的『價值觀』,還有自己對現實的看法。」
 現在,人們不再爲冒犯聖潔的上帝而感到罪責(不再在乎垂直方向上的關係),而是對別人如何看待他們的不良衝動或行爲感到羞恥或尷尬(只在乎橫向關係)。
現在,人們不再爲冒犯聖潔的上帝而感到罪責(不再在乎垂直方向上的關係),而是對別人如何看待他們的不良衝動或行爲感到羞恥或尷尬(只在乎橫向關係)。
「結果是,與其說今天人們在尋求寬恕,不如說是在尋求醫治,我指的是更好的內在自我意識和更好的自我體驗,」威爾斯說。「這給人帶來更多傷口,也讓很多人走向滅亡。」
美國人開始尋求藥物、自助書籍和治療師來處理這種羞恥感,而同樣在公立學校上學、看同樣電視節目的基督徒,也不能倖免於這種文化變遷。
基督徒沒有用聖經指導自己的生活,而是開始尋找和使用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情緒、思想和經歷。牧師們把焦點從研究和解釋聖經轉向了幫助人們駕馭他們的生活。教會放棄了教導艱難的教義,轉而實踐對福音朋友需求敏感的營銷術。新興教會則解構了敬拜、傳福音以及教牧事工的意義。
越來越多的神學院將課程從系統神學或希伯來文解經轉移到「靈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或神學與藝術之類的課目上。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莫勒(Al Mohler)指出,基督教書店過去放滿的是各種神學書籍,但漸漸地,很多不嚴肅的書開始出現在書架上,最後,神學書只留在了海報上。
「當你進入教牧事工時,那些關於福音如何對社區和文化產生影響力的見解非常重要,」克里斯·卡斯特多(Chris Castaldo)牧師說,他在《真理無處容身》一書問世後不久開始了在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的學習,畢業後前往戈登-康威爾神學院跟隨威爾斯學習。「威爾斯是以一種深思熟慮和清晰的方式提出和思考這個問題的聲音之一。他不怕把事情說出來,他不怕說『這不對』。」
威爾斯在《真理無處容身》中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爲現狀提供解決方案,這引起了一些讀者的批評。但那是因爲他還沒有完成整個系列(《真理無處容身》後來擴展成一個系列),也因爲他認爲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回到福音中去,過一個被恩典和基督的犧牲驅動的、以神爲中心的生活。
威爾斯估計《真理無處容身》大概賣出了7萬冊,包括印尼語、韓文和中文的譯本(本書沒有中文譯本,作者記錯了——譯註)。1994年,《真理無處容身》被《今日基督教》雜誌評爲神學和聖經研究類評論家獎第一名,《世界》雜誌稱它爲本世紀一百本最佳圖書之一。
 「它在保守的福音派中非常受歡迎,」狄馬可說。這本書給長老會牧師博愛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帶來了極大的共鳴,他開始給他的朋友們打電話。
「它在保守的福音派中非常受歡迎,」狄馬可說。這本書給長老會牧師博愛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帶來了極大的共鳴,他開始給他的朋友們打電話。
博愛思「把我們這些人都叫到了費城,討論形成一個聯盟的可能性,」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教授邁克爾·霍頓於1996年寫道。「雖然我們中許多人已經以某種方式參與了這類工作,但(威爾斯的書)一出現,就幫助我們圍繞一個共同的關注點組織起來。」
博愛思最後與100多位事工領袖,包括歐文·路茨爾(Erwin Lutzer)、辛克萊·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肯特·休斯(Kent Hughes)和當時才24歲的本·薩斯(Ben Sasse,現任參議員)於1996年聚集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Cambridge, Massachusetts),寫了一份聲明,肯定了宗教改革的五個「唯獨」,重申了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明顯差異,並指出了五旬節(靈恩派)神學的缺陷。
「看到蓋洛普和巴納等調查統計機構提供的數字,我們簡直嚇壞了,」博愛思在會議結束後不久寫道。「我們不能相信,有那麼多基督徒對神學基礎如此無知。這是我們的神學缺乏明確定義和框架的結果,我們發現福音派基督徒採納了世界上所有的做事方式。」
因此,這群事工領袖們成立了認信福音派聯盟(ACE),該聯盟將其博客命名爲「真理之地」(Place for Truth)。第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了博愛思、威爾斯、巴刻、莊玫麗(Mrs. Rosemary Jensen),阿利斯泰·貝格(Alistair Begg)、羅伯特·葛福雷(Robert Godfrey)、邁克爾·霍頓(Michael Horton)、阿爾伯特·莫勒(Al Mohler)和史普羅(R. C. Sproul)。認信福音派聯盟推出了一本在線雜誌,主辦了多個會議,並支持了「共同致力福音」(T4G)事工的啓動。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成員(例如里根·鄧肯和狄馬可)後來都加入了福音聯盟的理事會。
「大衛是這些YRR領袖(年輕、不知疲倦的改革宗人士——譯註)中不少人生命中的關鍵影響者和關鍵人物,」威爾斯的學生、俄勒岡州牧師邁克爾·勞倫斯(Michael Lawrence)說。無論是美洲長老會(PCA)還是美南浸信會(SBC)的牧師們都稱讚他是一位發出這樣吶喊的先知:我們必須回到神的話語作爲真理的首要地位,依靠神的靈——而不是我們的技術——來建立祂的教會。
威爾斯不像博愛思那樣善於組織,但他也沒有停止工作。
「我一直在努力,因爲我是除了葛尼斯之外,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在這領域發出呼聲的人,」威爾斯說。(《今日基督教》雜誌稱他爲「曠野呼聲」)「在我看來,這很重要,因爲這不僅僅是一個獨特的興趣,更是我們所處社會環境下合乎聖經的信仰應當有的未來。」
 「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就是現代化,而且不僅僅在美國。從韓國到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讀者都告訴他,他們對他的警告產生了共鳴。
「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就是現代化,而且不僅僅在美國。從韓國到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讀者都告訴他,他們對他的警告產生了共鳴。
於是,威爾斯在1994年寫下了《孤獨的神: 後現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機》(God in the Wasteland: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中譯本由天道書樓出版)繼續這個系列。這本書解釋了我們在現代世界中的經歷 如何影響我們對上帝的思考。答案是:我們失去了對超越性奇蹟的盼望,並很難想像與我們眼見所不同的任何其他東西。
他在1998年出版了《失去美德:爲什麼教會必須恢復其道德願景》(Losing Our Virtue: Why the Church Must Recover Its Moral Vision,此書無中譯),解釋了爲什麼給自己做診斷和接受療傷並不能解決我們的罪和墮落問題。
然後他寫了《超乎塵世的大能:後現代世界的基督》(Above All Earthly Pow'rs: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此書無中譯),它指出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是針對後現代世界無意義和空虛的唯一答案。他寫這本書是爲了回應讀者們,那些讀者很感激他指出了福音派的問題,但又想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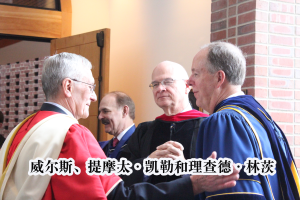 這些書等於是爲後現代讀者指出了系統神學的重要性,涵蓋了聖經、神論、人論和基督論的教義。隨後,威爾斯在《勇守真道》(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 Truth-Lovers, Marketers, and Emergent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中譯由臺北改革宗出版社出版)中總結了一切。
這些書等於是爲後現代讀者指出了系統神學的重要性,涵蓋了聖經、神論、人論和基督論的教義。隨後,威爾斯在《勇守真道》(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 Truth-Lovers, Marketers, and Emergent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中譯由臺北改革宗出版社出版)中總結了一切。
「我深受鼓舞,我不再是一個孤獨的聲音,」威爾斯在2008年告訴時任《今日基督教》編輯的科林·漢森。漢森將在那一年出版《年輕、躁動、歸正》(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這本書。
「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20、30、40歲的人,他們受夠了市場營銷式的信仰。……他們想要的信仰是有大能的、真實的、堅韌的,能夠抵擋現代化文化的挑戰,並且與這個世界提出的巨大問題相稱。他們往往是在重新理解改革宗那種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的過程中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真理無處容身》已經出版27年了,我們還不好說這本書能否會成爲傳世經典。威爾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針對的文化——搔首弄姿的電視佈道家、穿著夏威夷T恤衫的對福音朋友需求敏感的牧師,以及服飾誇張的新興教會領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寫一本書解決當時的問題帶來的問題是,問題發生了變化,書也會變得不再切合實際了。」狄馬可這樣告訴福音聯盟,但並不是所有的書都這樣。「加爾文寫書是要解決當時的問題,而且現在仍然很有幫助、很清楚,我認爲大衛的書也是這樣。」
1993年,邁克爾·勞倫斯在戈登-康威爾的一些同學認爲威爾斯很暴躁,把他們認爲是良性或中性的文化批判的過頭了。「但我認爲威爾斯沒有錯。」勞倫斯說。「文化不是中性的。我們無法逃避文化,我們確實要更批判性地思考文化。」
最近,德揚把《勇守真道》作爲閱讀作業分配給他在改革神學院教的學生,得到的反應大同小異:「班上有些人認爲,這傢伙什麼都不喜歡。一半的人認爲,『這些文化的確對我有影響』,『這本書真的很有見地』,或者『講的太有道理了』。」
 威爾斯寫的「太棒了,幫助我們從我們的生活中走出來一點,從一個稍微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勞倫斯說。「他幫助我們意識到,哦,這就是事情的真相。這就是爲什麼我有這樣的感覺。這就是爲什麼我的朋友們對我的福音佈道完全沒有印象的原因。……這就是他解釋文化的能力,聽起來很對。」
威爾斯寫的「太棒了,幫助我們從我們的生活中走出來一點,從一個稍微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勞倫斯說。「他幫助我們意識到,哦,這就是事情的真相。這就是爲什麼我有這樣的感覺。這就是爲什麼我的朋友們對我的福音佈道完全沒有印象的原因。……這就是他解釋文化的能力,聽起來很對。」
勞倫斯現在仍然在讀威爾斯的書。他正在努力重讀整套書,並要求他所有的教牧實習生都閱讀《真理無處容身》。8月,他和教會裡的一群人一起通讀了出版於1987年的《轉向神》(Turning to God,本書無中譯)。2012年,「共同致力福音」送出了數千本《轉向神》,幾年後,他們又送出了數千本《勇守真道》。
 「我們需要的信息是,我們的世界和我們事工面對的基本現實都沒有改變,」德揚這樣告訴福音聯盟。「我們很容易以爲一切都已經改變了。如果一切都真的改變了,那麼我們需要做的一切都得改變。」
「我們需要的信息是,我們的世界和我們事工面對的基本現實都沒有改變,」德揚這樣告訴福音聯盟。「我們很容易以爲一切都已經改變了。如果一切都真的改變了,那麼我們需要做的一切都得改變。」
他說,威爾斯給我們提供了解藥。「上帝還是一樣的,他的話語還是一樣的。我們從以前的時代可以獲得智慧——不是要借用某個特定的年代或特定的世紀用過的方法,而是要認識到人性、罪的問題、解決方法,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試圖走捷徑做事工,提供看似與我們的文化相關的東西,這對他們或我們都沒有好處,因爲我們需要的是對神和他的聖潔以及他的話語有更大的信心。」
他記得有一位同學問威爾斯:「我們需要採取什麼步驟來把事工都做對呢?」
「他用他那英式的、令人生畏的那種方式說,這問題正是問題的一部分,」德揚回憶說。「我們想要一個這樣的答案,一個能夠爲我們提供12個簡單步驟解決問題的答案。但沒有這樣的答案。答案是傳揚基督,培育看起來像教會的教會,以及把神當作神來認識祂。」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a Former Radical Sparked the New Calvinist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