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美國最高法院女性自由派大法官——譯註)的去世引發了許多關於對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的人之間建立友誼是否有價值的討論。在她的職業生涯中,作爲自由派人士的金斯伯格與她的同事、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保持著長期的友誼——在意識形態上,他們的共同點乏善可陳。
他們的友誼延伸到他們的家庭,他們有時一起慶祝新年。在一張令人難忘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斯卡利亞和金斯伯格在印度共度家庭假期時一起騎大象。我們所處的時代認爲「朋友」往往就是指和我一樣看待世界的人,他們的這張照片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形像。
近年來,他們這種「怪異的友誼」成爲許多專欄文章、廣播節目、甚至歌劇的主題。他們奇怪的、反文化的例子使人不由想問:他們爲什麼要有這樣的友誼?這種友誼是如何運作的?他們是通過無視差異而保持朋友關係,還是因爲差異而使他們的關係發展?他們如何理解一般友誼的性質?我需要來自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朋友嗎?當然,這些問題與基督徒有關:我們是否也應該重視這樣的友誼?
爲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思想一個基督徒和一個激進懷疑論者之間類似的、耐人尋味的友誼。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 1854-1921)是20世紀最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之一,他有位一生的朋友克里斯蒂安·斯努克·赫爾格隆傑(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 , 1857-1936),後者是一位自由派懷疑論者,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所處的時代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荷蘭,巴文克和斯努克兩位都是備受矚目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深厚友誼使他們成爲「怪異的一對兒」。
巴文克和斯努克都是牧師的兒子,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當時他們正在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就讀。儘管有這些共同點,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斯努克的父親是主流教派荷蘭改革宗教會的一名牧師,因「不忠實地拋棄」第一任妻子而被罷免,並與一名年輕女子(克里斯蒂安的母親)逃到倫敦。斯努克·赫爾格隆傑這一雙重姓氏屬於荷蘭貴族。作爲一個年輕的貴族,克里斯蒂安來自一個有名望的家族中一個有問題的分支。
相比之下,巴文克家庭出身卑微。赫爾曼的父親揚(Jan)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後來成爲規模較小、神學上保守的教派歸正會(CRC)的一位牧師。
巴文克和斯努克在學生時代就成了朋友,他們在餘生中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儘管他們在觀念上的差異多年來一直在增加。我們也沒有他們一起騎大象的照片。然而,我們確實有他們一生的信件,在這些信件中,他們分享個人的掙扎、試圖在信仰和政治問題上說服對方、閱讀和批評對方的著作,並分享生活中的快樂和煩惱。
他們的書信是一個窗口,讓我們了解到深刻的思想家和對基督教持有完全不同信仰的朋友之間豐富而坦誠的友誼。他們促使我們以基督徒的方式重新思考友誼的性質。在我們所處的文化中,友誼越來越多地圍繞著包裝好了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且這世界也鼓勵我們在「迴音室」中尋找朋友。
他們的學生時代從萊頓大學開始,這是荷蘭最古老、最負盛名的大學,大學的文化由貴族子弟主導:19世紀70年代典型的萊頓學生都有雙重姓氏,表明來自貴族家庭,並且同學之間往往有著血緣或姻親關係。一般來說,這就是斯努克的文化,但巴文克其實不屬於這裡。
然而,兩人都很快發現他們在大學裡是局外人。巴文克的家庭背景不夠「貴族」,而斯努克的家庭則被醜聞所玷污。同時,這兩個年輕人都對他們教授所教導的自由主義神學持批評態度。巴文克在教義和生活中致力於正統,而激進的懷疑者斯努克則對自由主義神學大膽而輕鬆的異端思想表示懷疑。
雖然兩人都是局外人(儘管原因不同),但巴文克和斯努克並不是因爲缺乏其他選擇而成爲朋友。巴文克並不是萊頓大學唯一的神學保守派學生,而斯努克還可以與其他自由派貴族混在一起。那麼,他們爲什麼選擇投資於這種特殊的友誼呢?
在萊頓的頭兩年,學生們在進入學位專業之前必須學習人文基礎課程。在那個時期,巴文克和斯努克首先是在其中的一門課程——阿拉伯語——建立關係的。巴文克覺得這門課很枯燥、很難學,他們的友誼始於尋找學習夥伴;很快就可以看出,他們對彼此都有很大的投入。
1878年,兩個年輕人都參加了同一個考試。巴文克獲得了優等獎(cum laude),而斯努克只是僅僅及格。巴文克認爲這是一種嚴重的不公正,認爲這是出於教授對他朋友的個人厭惡,並拒絕接受這位教授的課程證書,最終他被取消了優等生稱號。斯努克給巴文克的書面答覆是:「對我來說,這樣的友誼比紙上的文字更有無限價值。」在他們的學生時代結束時,他們的友誼已經變得非常忠誠。
隨著他們的生活前行,巴文克和斯努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巴文克成爲了一位著名的神學家,並以他獨特的正統、社會參與、基督徒敬虔而聞名直至最後一息。斯努克後來獲得了伊斯蘭研究的博士學位。他前往麥加,在途中皈依了伊斯蘭教,以便進入這個只有穆斯林才能進入的城市,在那裡他拍攝了第一批朝聖期間的麥加照片,不久他將這些照片出版成書,這爲他帶來了國際聲譽。
後來,他到荷屬東印度(現印度尼西亞)生活了多年,在那裡以穆斯林的身份生活(用Abd al-Ghaffar這個名字),與穆斯林妻子結婚並生下了穆斯林孩子。然後回到荷蘭,在那裡他恢復了自由的荷蘭身份,並與一位荷蘭婦女結婚。毫無疑問,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名的東方學家,而且在當時比他的神學家朋友要有名得多(儘管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改變)。
儘管他們的信仰和生活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反差,但巴文克和斯努克在他們的一生中仍然保持著定期的聯繫——包括當面,也通過信件。從他們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兩人都重視「批判性友誼」,並認爲當一個人被那些以同樣方式思考的人包圍時,他的洞察力很快就會變得枯燥。
他們認爲,一個真正敏銳的思想家需要一個他可以信任的親密朋友,但這個朋友並不認同他最基本的假設。巴文克曾將他們的友誼描述爲「既是對手又是朋友」的友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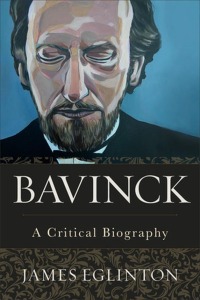 爲此,他們定期閱讀和討論對方的著作——往往會產生強烈的分歧。他們在伊斯蘭教、世俗化、聖經的權威性,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主張方面的互動讓我們毫不懷疑,他們的信仰是天壤之別。
爲此,他們定期閱讀和討論對方的著作——往往會產生強烈的分歧。他們在伊斯蘭教、世俗化、聖經的權威性,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主張方面的互動讓我們毫不懷疑,他們的信仰是天壤之別。
正如我在《巴文克:一本批判性傳記》(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指出,巴文克可能對斯努克在麥加和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生活一無所知。例如,他似乎沒有意識到斯努克爲了進入麥加而成爲穆斯林,而且在斯努克與一名穆斯林少女的婚姻問題上,斯努克對巴文克撒了謊,這似乎也是事實。顯然,他們的友誼並不總是容易繼續。
然而,它確實在繼續。巴文克的《啓示錄的哲學》(Philosophy of Revelation)一書是作爲一部針對懷疑論者的辯證法著作而寫的,似乎至少部分是爲了說服斯努克——儘管從他們後來對這本書的討論來看,他似乎並沒有被巴文克的論點所征服。
儘管兩個人都意識到他們的距離似乎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增加,但他們仍然致力於他們的「批判性關鍵友誼」,直到最後。例如,在巴文克去世的前一天,斯努克給這位朋友的妻子約翰娜·巴文克·席普斯寫信,講述了他最後一次去巴文克的病床前的情況。「我仍然被我的最後一次訪問深深地影響著:絕望,但也得到了啓發。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好朋友除了虔誠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特點,我和他的友誼從1874年一直到1921年。」
這樣的友誼當然有其耐人尋味之處。在巴文克-斯努克的故事中,我們看到兩個人提出了很多同樣的問題,包括神學和社會問題,但從完全不同的預設和角度出發:是否可能認識上帝?如果是的話,如何認識?宗教僅僅是一個人類文化的問題(斯努克),還是一個指向更高的東西的現實(巴文克)?
從他們的一生來看,他們的友誼是兩位思想家之間真誠而漫長的對話,他們有著雙重的動機:說服對方,以及向對方學習。一個世紀之後,這個例子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它在使巴文克成爲現在被許多人喜愛的有洞察力、敏銳和有說服力的作家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這也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也許就像在同一頭大象上看到觀點對立的大法官一樣罕見。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Befriend Your Opponents? Bavinck on 'Critical' Friendship.